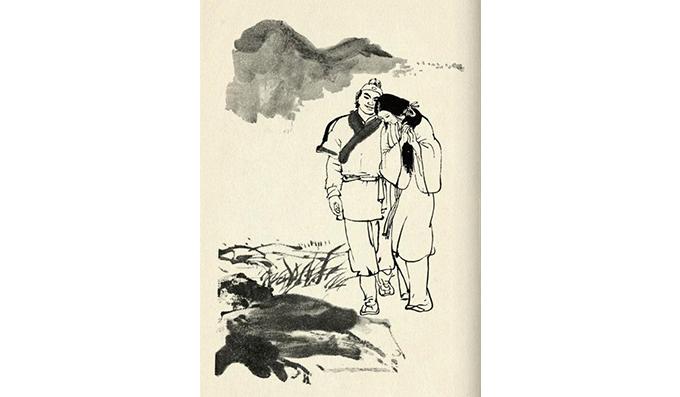專題.特輯
我初讀金庸是在一九八四年冬天。那時我是北大的新生,當時北大圖書館裏既有出版社剛剛重印的中西文學經典名著,也有剛剛翻譯出版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如袁可嘉先生主編的《西方現代派作品選》、王央樂先生譯的《博爾赫斯短篇小說集》等。圖書館裏有幾套香港出版的金庸,但永遠也借不到,想看就得到海澱租。所以,那段時間我白天上課之餘到圖書館二樓開架閱覽室讀中西文學經典名著,晚自習後回到宿舍讀租來的金庸—那時北大學生宿舍夜裏不熄燈,要到一九八五年秋天才開始實行夜裏十一點熄燈制度,並因此引發了北大在八十年代的第一場學生遊行。當時我並不知道,我在《西方現代派作品選》中讀到的「垮掉的一代」詩人金斯堡,正在離北京一百四十六公里的保定,在河北大學沒有暖氣的房間裏得了重感冒,並寫下了一首詩〈一天早晨,我在中國漫步〉。往前五年,一九七九年,境外文學開始重新進入中國大陸,這境外當然包括香港,包括在香港用漢語寫作的金庸。
因為寫過一本談論金庸、古龍的書《江湖外史》,我經常被問到金庸先生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先看看百年來中西文學史的時空軸,包括純文學和類型文學,找一找金庸先生在其中的位置。
金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在金庸先生出生的一九二四年,卡夫卡去世,托馬斯.曼發表《魔山》,博爾赫斯的第一部作品《布宜諾斯艾利斯激情》在前一年出版,川端康成剛剛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兩年後寫出《伊豆的舞女》,而T.S.艾略特的《荒原》和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已於兩年前出版,馬賽爾.普魯斯特已於兩年前去世。也就是說,在金庸先生出生的時候,純文學寫作風潮已經從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走向現代主義。類型文學中的推理小說也已經形成傳統:這一年,阿瑟.柯南.道爾爵士已經六十五歲,他的最後一個故事的時間線已經是十年前的一九一四年;阿嘉莎.克莉斯蒂已經出道四年,十年後她將寫出代表作《東方快車謀殺案》。再看中國文學,這一年,魯迅正在寫《彷徨》,其代表作《吶喊》已於兩年前出版,此時離一九一七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中國文學進入白話文(現代漢語)寫作時代僅七年。鴛鴦蝴蝶派小說《玉梨魂》在這一年被改編為電影獲得巨大反響,引發鴛鴦蝴蝶派作家為電影公司寫劇本和為報刊寫連載小說的風潮,這是現代漢語類型文學的第一個流派。
一九五五年,當金庸先生在香港開始為《新晚報》寫《書劍恩仇錄》,開創現代漢語新派武俠小說時,馬爾克斯出版第一部作品《枯枝敗葉》,納博科夫出版《洛麗塔》,羅布.格里耶寫出《窺視者》,海明威於前一年因《老人與海》獲諾貝爾文學獎,博爾赫斯已經完成所有重要作品、在雙目失明的同時當上了阿根廷國家圖書館館長。這一年,二十六歲的米蘭.昆德拉寫了一首歌頌捷克英雄伏契克的詩《最後的五月》,八歲的保羅.奧斯特剛剛上小學,六歲的村上春樹還沒上小學。這一年,阿嘉莎.克莉斯蒂已經著作等身功成名就,下一年她將獲得「不列顛帝國勳章」;「間諜小說」的代表作家約翰.勒卡雷正在牛津大學林肯學院上學,還沒開始寫作。這一年,在中國大陸,《人民文學》發表卡爾維諾的《把大炮帶回家的士兵》譯作。
一九七二年金庸先生以一部《鹿鼎記》金盆洗手,留下了「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十二年後我在北京讀到它們,同時讀到世界各國文學經典。這一年,中國大陸文學的代表作是長篇小說《金光大道》。
金庸小說的文學基因
從「傳統與個人才能」的角度看,金庸小說的文學基因有三個來源:一、白話文小說經典作品;二、西方寫實主義;三、白話文類型小說—舊武俠。
這裏面第一點最重要。中國文學進入白話文(現代漢語)寫作時代後,小說這一體裁因為有傳統白話文小說經典文本《金瓶梅》、《水滸傳》、《紅樓夢》等的傳承滋養,加上報刊刊載的大量需求,所以發展很快,到一九二二年,魯迅就寫出了現代漢語文學的經典作品《阿Q正傳》。相比之下,新詩的發展就很掙扎,因為沒有歷史經典文本可參考,得靠西詩的現代漢語譯文慢慢滋養。
白話文小說經典文本的傳統可以歸結為:語言風格—白描,敘事結構—章回體,終極價值關懷—佛教。金庸很好地繼承並光大了白描和佛教價值關懷,同時更多採用了西方現實主義的敘事結構(只在《鹿鼎記》中表面上採用了章回體),創立了新派武俠小說這一新的現代漢語類型小說。
從文學本體研究—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文學研究人性—的角度看,金庸小說在敘事方式上是成熟的、在文字風格上是出類拔萃的;在價值觀上光大了漢語文明傳統中最珍貴的深情重義和佛教價值關懷。在研究人性方面,按純文學的評價體系,金庸作品和所有類型小說的共同問題一樣:複雜人性的廣度與深度不夠;按類型小說的評價體系,金庸是以其個人品牌作為標籤導入讀者的閱讀和喜愛,這是非常罕見的文學史現象。一般情況是,你因為愛看推理小說,所以你從推理小說的分類標籤作為閱讀入口,找到了「福爾摩斯探案」,而不是因為你喜歡柯南.道爾,從而把他的所有作品都要找來讀完。
最終,從文學史的角度看,金庸開創建立現代漢語新派武俠小說,擁有可能是最多的漢語讀者,傳承了漢語文明中最珍貴的元素,並無意中代表了一九五五至一九七二年間現代漢語文學寫作的最高水準—想一想,金庸的本意和張恨水在報紙上連載《啼笑因緣》差不多—為了報紙的銷售。
難忘的閱讀快感和心靈撫慰
在文學史的時空軸中,金庸先生的位置在現代漢語純文學和類型文學的交叉地帶,純文學和類型文學的研究者、讀者盡可從各自的角度和評價體系來評價和閱讀金庸。這種評價和閱讀將一直持續下去,因為只要漢語存在,金庸就會流傳。
對我個人的來說,金庸曾經帶給我難忘的閱讀快感和心靈撫慰:走過大地不留痕跡的無名老僧;說「我偏要勉強」的趙敏和說「阿朱就是阿朱,四海列國,千秋萬載,就只有一個阿朱」的蕭峯;還有楊過的神啟瞬間—「某一日,風雨如晦,楊過心有所感,當下腰懸木劍,身披敝袍,一人一劍,悄然西去。」因為閱讀和談論金庸,我認識了很多友人,收穫了一生的友誼。
最後,對於作家作品,我有個人的最高標準:一、可以重讀的作家。可以重讀的作家不多,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博爾赫斯、魯迅可以;金庸可以。二、可以同時滿足美學和智力雙重挑戰的作品。《聖經》、《戰爭與和平》、《博爾赫斯文集》、《金瓶梅》可以;《天龍八部》可以。
(作者為北大詩人,網名「王憐花」,著有《江湖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