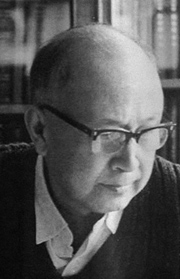思潮.動向
錢學森去世後,國內外有相當多對他的評價。其實要了解一個在時代風雲中生存下來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並不容易。作為一個科學家,錢學森的道路在他同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中有特殊性,如果我們深入理解錢學森和他生活的時代,會發現他個人的生活道路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是獨特的,沒有代表性的。就個人一生道路的選擇判斷,錢學森在一九五五年選擇從美國回到中國是恰當的,這個判斷建立在觀察錢學森後來的人生境遇上,如果他選擇繼續留在美國,他有可能做出另外的科學貢獻,但不可能有如此輝煌的人生。
錢學森的人生選擇
我們習慣於用愛國主義來判斷一九四九年後回到中國的知識分子,但愛國主義是抽象的,個人的現實處境是真實的,這個真實只有當事者自己心裏清楚。人生充滿偶然性,當現實困境中的個人選擇與國家命運聯繫的時候,常常會放大個人選擇中與崇高聯繫的一面,其真實的原因總是為人忽視。具體以錢學森為例,我們先要有一個常識判斷,他是在國民政府時代中國本土大學裏獲得大學教育然後順利出洋。在這個過程中,錢學森生活時代的開放性顯而易見,在他那個時代的人生選擇中,如果要強調愛國主義,那麼錢學森回國的時間應當更早或更為自覺,而我們現在看到的事實並不支持這個判斷,所以錢學森的出國與回國只在個人選擇的意義上具有討論的意義,簡單歌頌他人生選擇中的愛國主義,其實把複雜的人生簡單化了。
要理解錢學森,先要理解和他具有同樣人生經歷的其他中國知識分子。比如在科學家中,如果我們要講愛國,不能說只有一九四九年後從海外回來的知識分子才愛國,而那些當年就沒有離開的知識分子就不愛國。從一般常識判斷,好像沒有離開的更應該受到表彰,但事實恰好相反。比錢學森年長一代的中國著名科學家饒毓泰、謝家榮沒有離開中國,但他們自殺了,錢學森的同輩和朋友趙九章也自殺了,類似的情況,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中並不鮮見,這是我們紀念錢學森的時候應當反省的問題。
海外知識分子的處境
一九四九年後海外中國知識分子的真實處境,我們可以從考古學家鄭德坤當時給他的學生宋蜀華的一封信中看出。
鄭德坤在信中寫道:
一時不可能回國還有許多其他的原因,你知道我們在香港三年,一九四八—一九五一,多方想法子接洽要回國,始終不得要領,康橋的朋友聽到我困居香港,特想法成立了——遠東考古學美術講座,請我回來。工作是永久性的,現在國內安定,便告辭回國,在道義上也講不過去(周一良勸我退休後回國,那時老頭子不免有「今老矣無能為也矣」之歎了)。再者小孩們都在讀書,剛上軌道。我們的東搬西移,使我們浪費了多少年月,似不應再打斷他們的學業。……我的工作大部在東方學系及考古學系之間,課程是遠東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陶器、銅器及雕刻書畫等五種。學生並不多,前年還有位研究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公廳編輯的內部簡報《代表來信》第三十六號,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七日印刷)
不管錢學森當年回國的直接動因何在,我們從一般的人生境況理解更合常情,也就是說,選擇留在海外還是回到祖國只在個人的感受。詩人穆旦比錢學森回國的時間還早好幾年,但他後來成了反革命分子,一生窮困潦倒;學者吳世昌比錢學森晚回幾年,一位傳記作者說他,文革開始後「吳世昌進『牛棚』、下幹校、受侮辱、觸靈魂,備受艱辛,他的大女兒因經受不了運動的刺激而致病,至今尚住醫院,二女兒也喪失了攻讀學位的機會。」
從人生智慧的意義去理解
錢學森回國後的人生道路一帆風順,人們會以為這是他專業特點所決定的,這個判斷當然有相當道理。因為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確實以從事國防科研的科學家相對安全,比如鄧稼先、王淦昌、郭永懷等,但錢學森的安全是以他對中國社會的直覺判斷相關的,以錢學森的知識和對社會的理解,他不會不明白他所生活時代的特點,在同時代知識分子中,錢學森的人文素養是相當全面的一位,但錢學森準確判斷到了他所生活時代的極權特徵,所以除了專業以外,他的獨立性完全退回內心,以一切順應時代為基本生存方式。人們經常提到一九五八年錢學森的一篇文章,認為錢學森失去了科學家的良知,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提供了科學說明,我倒更願意在人生智慧的意義上理解錢學森,他要保存自己從事科學研究的權利,只能選擇這樣的方式,否則就是以卵擊石。我們可以想到錢學森一位同學徐璋本的遭遇。
徐璋本和錢學森同齡,同為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博士,且都是學導彈的,錢是搞導彈引導,徐是搞反導彈的,據嚴昌一篇文章介紹,錢學森和徐璋本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同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錢學森在航空與數學系學習,一九三九年獲博士學位;徐璋本一九四〇年獲博士學位。徐璋本歸國較早,回國後先在上海交通大學電信研究所任教。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後,徐璋本在清華大學物理教研室工作。
我曾在《中國科學院右派分子言論材料匯集》(中國科學院整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印,一九五八年)中讀到過徐璋本的一篇長文,它的內容後來曾以《徐璋本認為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會產生教條主義》(《內部參考》一九五七年二二二八期,頁二十、二一)上報中央。
徐璋本對時代的理解
徐璋本認為,第一,馬克思着重提出經濟上沒有人剝削人的、沒有階級的共產社會,在部分的理想上是正確的,但完全以唯物經濟基礎來闡明這個社會理想便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離開人性的「危險性」,這就是馬克思的學說和主義同他所提出來的高度理想口號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第二,馬克思根據「唯物的」、「生產工具和經濟制度的」、「社會階級鬥爭的」立場宣布,這種哲學、社會制度和方法,便可以達到大同共產社會的理想,人類地上的天堂,顯然是包含着嚴重矛盾性的一種學說。從人生自然哲學的一體性來看,馬克思忽略了「人」的關係而把人看做經濟制度的產物,這種倒因為果的學說不能作為「人生哲學」的指導思想。另外,強調「階級鬥爭」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戰爭進化論」同樣是脫胎於人類自私仇恨和殘忍本能的極端表現。這至多只能用之於被壓迫民族抵抗外來侵略過程,比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正是出於這樣的理論自覺,徐璋本認為,共產黨人掀起「階級鬥爭」、「思想鬥爭」的法寶,以為非此不足以鞏固「政權」,樹立「威信」,實行經濟建設,一切以馬克思學說聖典規範,嚴格奉行教條主義公式,結果使人民由感激愛戴變為畏懼沉默;由萬分積極和全民振作的奮發自新的景象一變而為奉行政府指令聽天由命的消極心理。而由於漠視人民情感,政權剛剛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對,對人民講威信,這又是馬克思的錯誤哲學和教條公式。到處發生「擾民」,摧殘人民的積極心,鼓勵消極自私心理,而事後補救辦法又是根據中國傳統的美德,勇於認錯改錯,將「人」與「人」的關係加以考慮,也就是不自覺地承認了馬克思唯物和經濟生產決定人生的錯誤!第三,徐璋本認為,馬克思治學態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國學術界的嚴謹詳盡有條理的優良傳統,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國普魯士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這種宗教色彩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應用在他的忘卻人類兩種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動政治哲學」上,就產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講目的、不講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學觀。第四,徐璋本認為,東方印度和中國特有的對人生本能的深刻體會,和毫無宗教迷信和教條主義的「大同人道主義精神」、「人天一體觀」大徹大悟,這個人生自然哲學思想是包括有關經濟生產的唯物論的部分的。
去留剎那間 人生大不同
徐璋本一九五七年成為右派,後被投入監獄,經歷二十年囚徒生活,改革開放後不久就去世了。同樣的教育背景,同樣的專業特長,同樣人生關鍵處的選擇,最後結局完全不同。根源在於他們對時代的理解和對世界的認知不同。我想,徐璋本就憑他那一篇文章,在將來的中國思想上當會有他的地位。他的人生,在俗世的評價中肯定是完全失敗了,因為他最好的時光在監獄裏度過,而錢學森卻在這一段時光中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偉業。後人只有感慨,而講不出什麼道理,其實也沒有道理,這就是人生。
錢學森對他生活時代的判斷是準確的,他的時代早就到來了;而徐璋本對人生的判斷是深刻的,他的時代沒有到來,他死後方生!徐璋本是思想家,他當為真理獻身,錢學森是工程師,他要為現實服務。據嚴昌文章敍述,徐璋本和錢學森私交不錯,但對徐璋本的遭遇也只能默默承受,他明白如何對待這個時代。二〇〇五年六月,《人民日報》曾刊載錢學森秘書涂元季的文章《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錢學森》,其中寫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他又向黨寫了長達八頁的交心材料,進一步談了他對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認識,尤其是對反右鬥爭的認識。因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鬥爭中還去看望錢偉長,在經濟上接濟現行反革命分子,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的家屬,政治立場不堅定,思想上劃不清界線。錢學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檢討了自己的錯誤。」
錢學森和徐璋本是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他們的人生道路自然也就不同。巫寧坤在他的回憶錄《一滴淚》中有一個經典細節,一九五〇年,李政道送巫寧坤回中國大陸,巫寧坤問李政道為什麼不回,李政道回答不願意讓人洗腦。一九五七年李政道和楊振寧一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那時巫寧坤已在農場勞改。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之初,受盡磨難的巫寧坤立即選擇離開中國,而到了一九八九年後,當年選擇離開的楊振寧卻選擇回中國大陸定居,這就是一個人對時代的感覺和判斷,在這一點上,錢學森和楊振寧一樣,有非常好的直覺,他們選擇最好的,這或許就是錢學森他們那一代科學家的宿命,去留均在剎那間,人生也就截然不同了。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於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
(作者是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