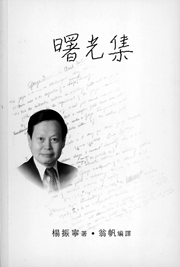語文.書話
最近楊振寧教授和翁帆女士合作出版《曙光集》,裏面收集了將近五十篇楊先生的文章、書信、訪問記,以及數篇與他相關的文字,其中關於科學與科學家的大約佔六成,關於歷史、文化、中國現狀和前景的佔四成,從中可以窺見這位物理學大師過去三十年間對物理學基本理論的反思、對前輩和朋儕的情誼,以及對國家民族前途的關懷。更重要的是,這本集子由翁女士編譯,無疑也就是她和楊先生結合的象徵。潘國駒兄建議我為此集寫點東西,我不假思索就答應下來。對於像我這樣從物理學轉到文史領域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閱讀此集正有如孫髯翁所謂「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一時間讚歎、驚訝、迷思、感慨交集。更何況,我有幸認識楊先生多年,為這些散亂思緒作個記錄,對個人,對讀者應該都是有意義的。
世中遙望空雲山
物理學的終極追求是從自然界萬象中找出基本規律。這從古希臘的自然哲學開始,到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而獲得第一個突破,兩千年後牛頓的《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帶來第二個突破,至於二十世紀初的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之發現則已經是第三次突破了。這三次突破或曰「科學革命」,代表人類認知模式之根本變革。楊先生因緣際會,剛好趕上參加第三次科學革命的後續階段,以是得成大學問,享大名聲。《曙光集》中討論「分立對稱性」(discrete symmetries)、「規範場」(gauge field)和統計物理學發展史的十來篇文章便是他躬與其役的現身說法。其中《愛因斯坦對理論物理的影響》、《分立對稱性P, T和C》和《魏爾對物理學的貢獻》等三篇更將他自己的思想歷程與貢獻放在前人工作與基本理論整體發展的大背景中來討論,那是非常深刻和有味道的科學史料,但對於此專門領域以外的讀者而言,則恐怕有如隔霧看花,難免「世中遙望空雲山」之歎。
當然,這是無可奈何的。理論物理學之所以精確、奧妙,是因為它建立在數學語言而非自然語言之上,這也就是史諾(C. P. Snow)所謂「兩種文化」之間的鴻溝。柏拉圖在《對話錄》(The Dialogues)的《米諾篇》(Meno)中通過與童奴問答來說明,正方形面積加倍時,其邊長等於原正方形的對角線,而並非原邊長的雙倍。這基本上反映畢達哥拉斯教派(Pythagoreans)已經發現√2是無理數這一事實,它是追求嚴格幾何論證的動力,也是數學發展成另外一種語言,由是導致西方第一次科學革命的起點。柏拉圖在該篇的原意是證明即使高深知識亦並非外來,而是本來就存在於記憶之中,因此人必然有前世,故而靈魂不朽。然而,數學發展一日千里,今日已經達到繁複深奧之極致。時下在物理學界大行其道但始終未能與現實世界接軌的超弦理論就曾經令楊先生感歎:與其這樣倒不如乾脆改行學數學好了。看來,假如能夠起柏拉圖於九泉之下,他有關記憶、前世、靈魂諸學說恐怕也得重新修訂了。
對稱觀念的史前史
不過,以上所說只是就理論物理的精義而言。其實,與楊先生兩個主要發現相關的一些根本觀念,像「對稱」、「對稱破缺」、「對稱支配相互作用」等等,大體上都可以從直觀得到理解——集子中《對稱和物理學》一文所致力的,正就是為一般讀者提供這樣的理解。如楊先生在該文所着意指出,這些觀念有很長遠的淵源:它們不但已經為二十世紀初的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魏爾(Hermann Weyl)意識到,而且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出現的晶體學和群論、十七世紀刻卜勒(Johannes Kepler)的宇宙諧協觀念,乃至古希臘天文學之以疊加的圓形運動為天體運行軌道。
在此,我們可以為楊先生作個有關對稱觀念「史前史」的注腳。柏拉圖在《法律篇》中借一個陌生人之口宣稱:「那些關於日月和其他星辰游離(正軌)的教導並非真理,而是真理的反面。它們每一個都依循同樣軌道——不是許多軌道,而僅僅是一條軌道,那是圓形的;所有其他變異(軌道)都只是表象而已」(Laws 821e-822a)。這可能是「對稱支配自然規律」這一思想的最早成文論述,當然,它還是很粗糙、模糊的。從此思想出發,學園(Academy)中的數學家尤多索(Eudoxus of Cnidus)提出天體運行的「同心球面」(homocentric sphere)模型,亞歷山大城的阿波隆尼亞斯(Apollonius of Perga)發明「主輪—本輪」(deferentepicycle)模型,此模型又為托勒密(Ptolemy)在《大匯編》(Almagest)這本鉅著中有系統地應用於當時所有已知天文現象上。
此後這古代對稱觀念還經歷了數次轉折。為了追求與觀測高度吻合,托勒密至終被迫作出違反嚴格「圓形疊加」原則的一些修訂,即提出了所謂「曲軸本輪」模型,它可能是最早的「對稱破缺」機制。但到了中世紀,伊斯蘭天文學家對托勒密之偏離基本原則作出嚴厲批評;他們還進一步發現,完全符合「圓形疊加」原則的所謂「圖西雙輪」(Tusi couple)機制可以重現托勒密機制的效果。這樣,他們得以將破缺的對稱修補完整,也就是「破鏡重圓」。而且,此思想與機制還為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所全盤承受。因此,到十七世紀,刻卜勒之毅然捨棄完美對稱,而提出行星軌道為橢圓,那實在是肩負着二千年歷史重擔,要以萬牛迴首之大力來作出的突破。
楊先生說:「造成分立對稱破壞的基本原因今天仍然不知道,事實上,對這些破壞連一個可能的基本理論上的建議都沒有」(《曙光集》,八方文化出版,頁四一,以下徵引此集只舉頁數)。回顧對稱破缺的漫長「史前史」,我們不免興起一點狂想:當代物理學中的對稱與破缺真是本質性的嗎?抑或在某個更廣義的數學層面上,也存在類似於「圖西雙輪」那樣的機制,可以移除表面上似乎無可置疑的破缺?又抑或恰恰相反,物理定律在本質上其實並無我們所熱愛和想像的對稱性,只不過在特殊狀態下它表現為細微的對稱破缺,正如天體的橢圓或者更複雜軌道表現為圓形的疊加呢?
天球和諧的淵源
《對稱與物理學》還提到,刻卜勒試圖以層層相套相接的五種正多面體與球體來決定五大行星與地球軌道直徑的比例。這是刻卜勒在一六一八年完成的《宇宙之和諧》(Harmony of the World)一書所提出來,當時他的行星運動第一和第二定律已經在多年前發現,第三定律則在此書首次發表,所以這是他成熟時期(四十七歲)的作品。此書核心思想來自公元前五世紀的畢達哥拉斯教派,那也是歐幾里得和柏拉圖的思想淵源。例如,五種正多面體最早出現於《對話錄》的《蒂邁歐篇》(Timaeus),而根據考證此篇(最少其大部分)是由畢氏教派後代弟子費羅萊斯(Philolaus)傳給柏拉圖。又例如,《宇宙之和諧》從幾何學、算術、樂理、天文(包括相關的星占學)等四方面論述宇宙結構,這四種學問合稱「四藝」(quadrivium),那正是由畢氏教派所首先發展,並且被公認為其印記。最重要的是,此書以「和諧」為中心觀念,那來自畢氏教派的「天球諧樂」之說:他們認為物體移動速度和所發聲音高低是相關的,既然天體不斷以高速運轉,那麼就會持續發出樂音,而這些是彼此和諧的,其音程(interval)比例可以用1、2、3、4這四個簡單數字來建構。因此亞里士多德說,對畢派而言,「整個天(whole heaven)都是樂音階律,都是數目」(Metaphysics 985b25)。令人驚訝的是,已經作出大發現的刻卜勒對於二千年前的畢氏教派宇宙觀仍然深信不疑:《宇宙之和諧》不但以五種正多面體來計算行星軌道的平均直徑(並且由於巧合獲得相當滿意的結果),更在他最新發現的行星運動三規律基礎上,詳細計算天體所發樂音的音程,和論證它們的和諧。
刻卜勒如此,完成十七世紀科學革命的牛頓也一樣。他不但如楊先生所說,長期沉醉於煉金術和神學(頁二一七),而且還認為他自己所發現的「世界系統」是古代聖賢如費羅萊斯、阿理斯它喀斯(Aristarc-hus of Samos)、柏拉圖、其他畢派學者乃至埃及神廟中的祭司等等都早已經知道的,這就是所謂「本始智慧」(prisca sapientia)的觀念。他的鉅著《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並非以他所發現的「流數法」(method of fluxions)即微積分來建構,而仍然是以傳統幾何學方式論證,這也是他對古代學術高度重視的明證。刻卜勒和牛頓的情懷、態度是值得強調的。它反映了西方科學雖然好像是在公元六至十一世紀中斷,但在十七世紀科學家觀念中它仍然是個有延續性的大傳統。事實上,就西方科學的問題意識和方法而言,也同樣如此,古代幾何學對牛頓《原理》以及在加利略著作中的重要性只不過是最明顯例子而已。所以,現代科學雖然是由十七世紀科學革命所產生,但它的淵源並不止於文藝復興,甚至也不在中古歐洲,而得一直追溯到畢達哥拉斯教派。
科學與中國文化
楊先生經常提到,他平生所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令中國人不再覺得他們不如人。換而言之,他以個人成就證明,中國人的科學才能絕不比西方人遜色。因此,很自然的,他對當代中國人和華人科學家獲得卓越成就者像陳省身、吳大猷、吳健雄、鄧稼先、黃昆、丘成桐、崔琦等都十分留意,各有論述,對於那些曾經作出重要發現或者建議,但與國際榮譽失之交臂的前輩科學家例如趙忠堯、王淦昌、謝玉銘等,更作了專門研究,或者着意追尋其事迹,這些文章除了極少數例外都已經收入《曙光集》。但很顯然,更大也更根本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科學不如西方?以楊先生的中國情懷之深,他自然不會忽略這核心問題,集中有兩篇文章就是環繞此題目而發。
兩篇中較早的是一九九三年在香港大學的演講稿《近代科學進入中國的回顧與前瞻》。此文第一節接受了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觀念,認為「中國科技直到一四○○年前後比歐洲科技優秀」,但「到一六○○年中國科技卻已遠遜於歐洲」,原因則是一四○○至一六○○這兩百年間歐洲發生了文藝復興,而在中國則知識停滯不前(頁二一三至二一五)。但楊先生的文章絕大部分仍然強調古希臘幾何學對牛頓的重大影響,以及一六○○至一九○○年間中國傳統觀念對西方科學的抗拒,以致現代科學要到一九○○至一九五○年間才真正進入中國。像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一樣,楊先生可能出於李約瑟在實證研究方面所作巨大貢獻的尊敬,而沒有覺察到他科學發展史論中的嚴重問題。例如,中國某些技術的先進是否就等於其「科技」即科學與技術的優秀和優勝?倘若古希臘幾何學對於牛頓真是那麼重要(而那的確是事實),那麼中國科學怎麼可以說是在一四○○年以前一直比歐洲優秀呢?而倘若它直到一四○○年還是比歐洲優秀,那麼在十七世紀接觸到歐洲科學特別是翻譯了《幾何原本》前六卷之後,又怎麼可能仍然不明白其先進性之所在,而仍然故步自封達三百年之久?事實上,李約瑟本人倒深明這些問題之要害,因此,為了消除其理論中的矛盾,他不得不強調以下兩個其實絕不可能成立的觀點,即希臘數學對於近代科學的出現其實並不那麼重要;以及到了明末即一六四四年「中國與歐洲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已經再沒有任何可覺察的分別;它們已經完全熔結,它們融合了。」(分別見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 Allen & Unwin 1969, pp. 50-51;Clerks and Craftsm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398)。很顯然,在這兩個問題上,前述楊先生的觀點和李約瑟是完全對立的。
至於《〈易經〉對中華文化的影響》則是十多年後發表的文章。楊先生在此文中提出,「《易經》影響了中華文化的思維方式,而這個影響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跟着又提到阻礙中國科學發展的多個其他文化與制度因素(頁三六五至三六七)。這些觀點惹起了不少論爭,但我們無法在此討論了。然而,應該毫無爭議的是:上述因素(例如《易經》和「天人合一」觀念)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都是長期和自古已然的,因此,它們倘若的確對科學發展有重大不利影響,那麼就很難想像,中國科學在一四○○年以前是一貫比歐洲優秀了。
其實,中國科學為何落後於西方的問題在一九一五年就已經由任鴻雋在《科學》雜誌創刊號上提出來,以後經常掀起熱烈討論,許多文化和制度性因素都曾經被考慮,只是到了五十年代以後,李約瑟的鉅著相繼出版,他的「中國科技(在十五世紀以前)長期優勝,歐洲在文藝復興之後才超前」論調才風靡一時。但此論雖然對國人而言非常中聽,卻明顯不符合事實,也完全不為西方科學史家接受,所以是需要仔細剖析和辨正的。中國和西方文化是兩個龐大、源遠流長的不同體系,科學在這兩個體系中的發展歷程更是千頭萬緒、錯綜複雜。因此,這兩方面發展何以會出現巨大差異恐怕無法歸咎於少數明確原因,甚至也可能並無簡單、明瞭答案。科學史和科學不一樣,它牽涉人事和社會整體,而那是缺乏清晰規律,也難以從基本自然規律推斷其發展的混沌現象。
結合兩個世界的努力
楊先生有很強的自我意識。他既是西方科學火炬傳人,更是肩負國家民族前途重任的中國知識分子。由於中國過去三十年來的進步,他更深切感到,這兩個理念,這兩個不同世界,是可以統合起來融為一體的,而自己對於促成其實現既是當仁不讓亦復責無旁貸。在《曙光集》二十來篇有關中國前途與科學發展的文章和訪問記之中,這種樂觀、信心和使命感可以說處處躍然紙上。對於大部分中國人來說,這期望無疑是順理成章,而楊先生雖然終身浸淫於粒子理論的曲折奧妙,但心底裏鼓動他的,當仍然是儒家念念不忘家國的承擔,和「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我曾經趁《二十一世紀》雙月刊召開編輯委員會的機會請問楊先生,他是否覺得影響自己一生最深的是儒家思想,他毫不猶豫的肯定了這說法。
然而,現代科學是在崇尚個人價值和判斷的觀念上締造出來的。畢達哥拉斯教派和柏拉圖之所以嚮往宇宙奧秘是因為他們深信這是通往永生之道,中世紀以至十七世紀歐洲科學家探究自然哲學則是為了彰顯上帝的大能與榮耀。現代科學從大約十八世紀末開始影響技術,其現實意義日益增長,但歐洲科學傳統則仍然以崇尚心智(intellect)和批判意識為依歸,這在愛因斯坦身上表現得最透徹:他積極反對德國軍國主義和納粹政權,響應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反核子武器宣言,甚至對庇護他的美國也嚴詞批判。在當代,科學、技術與社會、政治已經融為一體,然而科學家的獨立判斷和求真精神仍然是其道德權威的基礎。最近國際氣象學家團體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在全球暖化這高度敏感與政治化問題上所發揮的獨立與巨大作用當是明證。因此,將發揚科學和民族復興這兩個理念統合起來在表面上是再也自然、合理不過,但由於兩者分別屬於「天」、「人」這兩個不同範疇,它們既互相補足,同時又具有深層矛盾,所以統合絕非簡單或者容易的事情。
楊先生是時代寵兒,無論事業、際遇、家庭都圓滿幸福,他自認為「這麼多幸運結合在一起是很少有的」(頁四一七),這和近代中國另一位望重士林的學者胡適之頗為相似。不過,很不幸,他似乎也同樣未能逃脫胡先生「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命運。這可能是他肩負一言九鼎之重,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未能暢所欲言,或者各方對他在國家、社會、教育政策上的作用寄望孔殷,由是產生不實際期待和連帶的失望所致吧。無論如何,拳拳服膺真理,究心自然規律的科學家,和憂國憂民,為士林表率的大儒是兩種完全不相同的理想人格。楊先生要將兩者凝聚於一身無疑是個嶄新、困難、容易招致誤解的嘗試,不過,由於他的時代、背景、地位和獨特經歷,這恐怕也是命中注定的了。如今楊先生年事日高,但健康如恆,自信、樂觀、勃勃興致不減當年。我們祝願他在翁帆女士陪伴下花好月圓人壽,繼續以大無畏和獨立探索精神為中華民族作出貢獻。
二○○八年暮春於用廬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