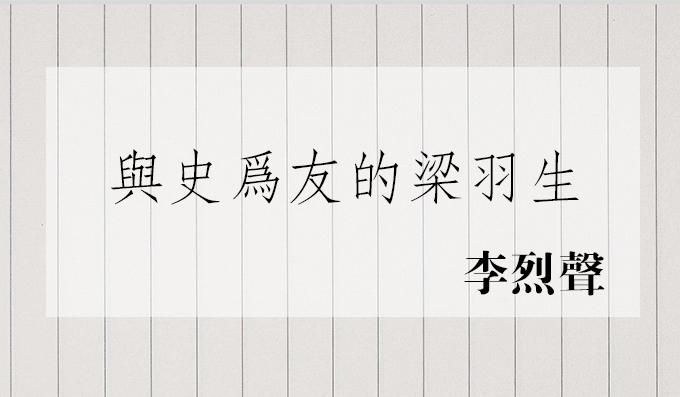附冊:明月灣區
前些日子,我寫了一篇有關與查良鏞先生交往的短文,純為紀念離世師友印象而作,並無憑藉故友關係而撈取名利之意。今天,我又寫一位與查先生齊名的武俠小說家梁羽生的紀念文章,仍是純屬紀念故友而作。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由於國共之爭,社會上出現一種非黑即白的現象,其中特別以報界為然,明明是很熟的朋友,如果你進了左報,右報朋友便一夜之間友情消失殆盡,陌路相逢,你不知天高地厚,向他打個招呼,冷不防他白眼看天,扭過頭來,向路溝「喀吐」一聲,吐一口濃痰,令你非常難堪。反之亦然,於是,交朋友交得辛苦異常。
那時候,我在澳門一家右派報館當副刊編輯,薪酬既低,糧期又不準,常常弄到「一索咁身」(身無分文),只得盡量找外快,窮鬼書生,找外快只有替報紙寫稿一途,我既乏人事關係,又無貴人帶挈,只好漁翁撒網,左報右報不限,把稿子寄去,如蒙青睞,稿子出街,收到稿費單,便多一筆收入。可幸天無絕人之路,我寫的文史掌故散文,只談前朝恩怨,不提現代政治,頗合總編輯大人胃口,右報如《天文臺報》,左報如《大公報》,都蒙採納,被朋友譏為「左右逢迎,細大不捐」,譏笑由他譏笑,稿費我自領之。
我居於澳門,領稿費需過大海往港,有時,領稿費剛巧遇到編輯在場,便由寒暄而成為朋友,右報認識陳孝威、姚勵頗,左報認識羅孚、梁羽生。
梁羽生給我的印象是個文質彬彬的書生,我知他故鄉是廣西蒙山,我幼年隨父到過梧州,知道蒙山棣屬梧州,梧州人大多會說廣東話,我用廣東話與他溝通,並無困難。
一回生,兩回熟,偶而梁羽生編務清閒,相約到冰室喝咖啡,那時,他好像還未從事撰寫武俠小說,我們談話,三句不離本行。話題都是離不開文史與掌故,從言談中,我發覺他對於古人詩詞非常嫻熟,遠遠比我讀過的為多,我深愧不如,他把我引為同道,說:「我們這類人,都是與史為友。」
記憶中有一回我們談到三國時代劉備的孫夫人,和後人對她的評價。他說,「某地孫夫人祠有一副對聯」:
思親淚落吳江冷 望帝魂歸蜀道難
「此聯貼切而淒婉,真是才人之筆。」我完全同意,我同時也舉出黃仲則〈靈澤夫人祠〉(孫夫人殉夫沉江,後人建祠紀念她,祠名「靈澤夫人祠」)詩中一聯:
一慟無由恩已絕 兩家多故事難言
比前者更感人,直揭孫夫人心事,梁羽生先生也說:「深獲我心,可知英雄所見略同」,我們相視而笑。
有一次,我又赴港領稿費,梁羽生先生問我:「XX先生家住調景嶺,他有一筆稿費存在我手中,你如去訪他,請你順便帶給他。」我和XX先生是忘年之交,他臥病調景嶺,我正要去探視他,便一口答應,接過鈔票,順手帶一份當日副刊登載XX先生文章的報紙上路。
早年,調景嶺還是一片荒山野嶺(據說曾有洋人在該地因生意失敗而自縊,又稱「吊頸嶺」),我對該地環境非常陌生,不虞有他。我由中環前往,既要乘車,又要乘船,更要走路,其時正值南國夏季,烈日當空,驕陽如火,曬得石頭快要熔化,我一面走路,汗流浹背,正想找個地方歇歇腳、喝喝水,無奈遊目四顧,除了弱草便是石頭,盡是紙皮鐵片簡陋小屋,沒有士多仔、咖啡店或冰室,正煩惱之際,忽然聽到一聲吆喝:「來!喝杯茶吧!」
我喜出望外,循聲一看:一株榕樹下有一個茶水檔,一個老人家手持葵扇向我招手,招呼我坐在舊木箱上,斟一大碗茶,我如渴驥奔泉,一飲而盡,坐下休憩。誰料老人家拿起我手中的報紙一看,老臉頓時變得醜惡不堪,粗聲罵我,怒目相向,一副殺氣騰騰氣象,我正要掏錢付帳,他大掌一揮:「滾!我不要你的臭錢! 」
對此不可理喻之人,只好避之若浼。
找到XX先生,把稿費交代清楚,提起喝茶受辱一事,他哈哈大笑:「忘了告訴你,這裏有些人,已到不可理喻之境了。」
我後來把此事告訴梁羽生先生,他也為之搖頭苦笑。如今,調景嶺舊地變新顏,梁先生已主懷安息,但我每次到調景嶺,還是想起梁羽生交付給我代送稿費的往事。
(作者又名李瑞鵬,詩人,九十多歲,作品曾多次獲獎,並有作品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