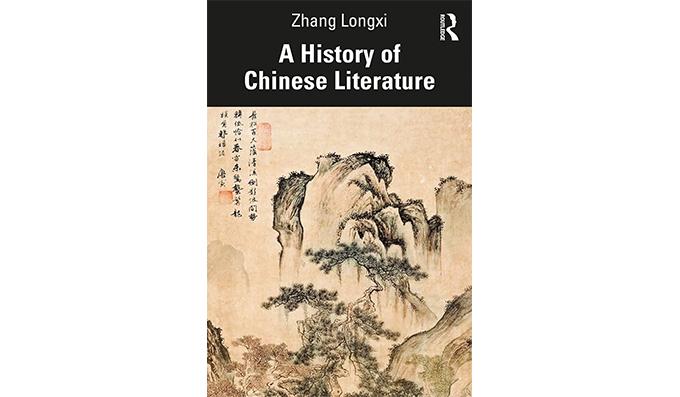附冊:明月灣區
前言:張隆溪教授是國際著名的比較文學學者,長期研究西方的文學理論與世界文學,撰有中英文著作二十多種。二○二三年,他出版英文專著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國文學史,London: Routledge),以一人之力,梳理三千年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超越歐洲中心論,向西方讀者推介中國的經典作品。專訪裏,張教授會剖析他的「文學史觀」,並會比較中、西方各種的文學觀念。
李浩榮(以下簡稱「李」):在大作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出版以前,西方學術界主要有兩本以英文寫成的中國文學史,分別是《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和《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這兩部書對您的寫作有參考價值嗎?請談談二書之優劣。
張隆溪(以下簡稱「張」):《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和《劍橋中國文學史》對我的文學史寫作,不但沒有參考價值,甚至可以說,我的寫作是針對這兩本書的寫法而作出的。我是研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出身的,所以對西方的文學發展史比較熟悉。十九世紀是一個撰寫歷史、文學史的黃金時代,當時很有名的德國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說過一句名言:「歷史敘述就是把歷史如實地講述出來。」(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十九世紀著名的文學史作品有很多,其中有法國學者丹納(Hippolyte Taine)編撰的《英國文學史》(一八七二)。丹納提出文學的產生有三個要素,即民族的、環境的和時代的,這都是跟作者所生活的地理、文化、時代息息相關的。
還有一本經典作品,由意大利學者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撰寫的《意大利文學史》(一八八三)。桑克蒂斯的《意大利文學史》裏寫到但丁,說但丁寫《神曲》可能有作者本身的一些想法,然而《神曲》完成以後,其意義已超出了作者本身的意圖,所以我們討論《神曲》時,大可不必以作者的意見作為基礎。桑克蒂斯的看法對二十世紀的文學理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到了二十世紀,文學理論得到充分的發展,如新批評與形式主義的產生等,但卻變得不太利於文學史的寫作。可以這樣子說,二十世紀的文學理論,其關注由作者轉向文本,然後再從文本去到讀者身上。尤其是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對於什麼是真實、有沒有可能真實地重現歷史等議題,產生了很大的質疑,甚至歷史的邏輯、因果關係等,皆受到強烈的批判。對文學史批評得最厲害的代表人物就是海登.懷特(懷特是我在加州大學時的同事),懷特認為,歷史的敘述跟小說的敘述沒有太大的分別,不過是把不同事件有條理地串聯起來。這就恍如亞里士多德所言,悲劇是對一個完整行動的模仿一樣,有開頭、中間和結尾。
傅柯也抱持類似的觀點,認為知識與權力存在共謀關係,誰掌握權力,誰就有話語權。所以俗話說,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這種說法不是全然的錯誤,但影響極壞,抹煞了歷史與文學的界線,使歷史顯得不再可靠。有一回,懷特去演講,說歷史的敘述很多都是虛構的,台下一位老太太舉手發言,露出手臂上的一行數字,問懷特:「你的意思是說,我手上這行數字是虛構的嗎?」那些數字是老太太給關進集中營時,被納粹烙在手臂上的。懷特當時顯得尷尬萬分,幾乎下不了台。當然,懷特的意思並不是要否定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但他的理論確實有歷史虛無主義的傾向。
馬克思主義的左派評論家詹明信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缺乏歷史感。他講的是西方的情形,所以,二十世紀的歐美學界幾乎沒有一個人寫成的文學史。在這個背景下,有兩部很重要的文學史誕生了,其中一部是《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Emory Elliott. The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不是Emory Elliott一個人寫的,而是他召集一群人共同寫成的。另外一部是《新編法國文學史》(Denis Hollier. 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這兩部著作摒棄了過往那種宏大的敘述,不再採用「死去白人男性」的觀點,不再重複那些父權、建制、殖民、帝國主義的思想。這兩部著作是由數十個學者一起參與的,每一個人就寫自己的專業知識,例如剖析當時的社會情況、出版業的興衰、印刷術的發展等,五花八門的學問,但談文學的篇幅就相對少了。哈佛大學教授戴維.珀金斯在九十年代寫了一本薄薄的書《文學史還可能嗎?》(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珀金斯的答案是不可能了。他以上述兩部文學史為例,稱之為「後現代式的百科全書」,書裏盡是條目式的知識,但知識之間沒有連貫性。這兩部文學史的寫法還是有影響力的,如《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與《劍橋中國文學史》就是採取相同的方式,召集一群學者共同寫成,旨在呈現一種多元的歷史觀。然而,我認為這種敘述方式是不適用於中國文學史的。
專注於分析作品和文學形式的發展
李:《劍橋中國文學史》強調以「文學文化史」的角度切入中國文學,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分析作品時,我看主要採用「知人論世」的方法,您撰寫此書時,有否考慮過研究方法的問題?
張:美國文學史、歐洲文學史可以用百科全書式的寫法,因為西方讀者熟知歐美的著名作家與作品;但是,在外國讀者完全不了解中國文學的情況下,還大談特談中國古代的出版市場、書籍的印刷等,那就是不恰當了。所以,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裏,我專注於分析作品本身和文學形式的發展。以「詩」為例,最早的《詩經》以四言為主,到了漢代,發展出五言、七言詩來,而且開始注重聲調。中、西詩人寫詩的方法是不同的。中國人寫詩注重聲調、平仄,西方人寫詩則留意輕、重音,如抑揚五步格(iambic pentameter)。西方還有無韻詩(blank verse),如莎士比亞的劇本和米爾頓的《失樂園》都是不押韻的好詩。中國的詩尤其是律詩的發展,跟聲韻平仄是密不可分的。沈約曾經寫過《四聲譜》,雖已失傳,但我們知道早在南北朝時期,中國人已關注四聲的區別。在書裏,我還分析了詞、散曲、小說這些文體的發展,譬如講到小說這通俗文學的成熟,就是跟商業、城市和市民生活的發展有關係。
「我想給西方讀者介紹純粹的中國文學史」
李:《劍橋中國文學史》主編宇文所安自言,其書的特色之一在於展現西方的學術視野,例如有專文介紹西方喜愛的唐代詩人寒山。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則沒有提及寒山。西方學術視野或西方市場口味,是不是您撰書時關注的項目?
張:我的書裏提到許多中西文化交往的歷史,如寫元代時,提到馬可波羅遊歷中國,又如講到《趙氏孤兒》時,敘及此劇翻譯成法文以後,受到伏爾泰等文豪的熱愛。但是,我在書裏沒有提到寒山,因為唐朝大師輩出,論詩人,寒山是完全排不上號的。美國文化界喜歡寒山,如詩人蓋瑞.施耐德 (Gary Snyder)便對之吹捧有加。五十年代,施耐德在柏克萊讀書,問老師陳世驤該去研究哪位中國詩人,據說陳世驤覺得若推薦杜甫、李白,對施耐德來說未免太深了,就推介寒山給他,果然合他的口味。寒山走紅還有時代的因素,那時剛好碰上嬉皮士流行的年代,美國的年輕人喜歡穿著袈裟,扮成洋和尚,讀一點東方的禪詩。但是,我寫中國文學史,絕不會按美國人的喜好來決定內容。況且宇文所安對中國語言和詩的理解,我向來是抱持懷疑的態度。說到底,寒山在中國文學史上毫無影響力,如果中國人寫文學史去談寒山,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另外,我的書裏刻意避免引用西方的文學理論去闡釋中國文學。我在美國加州大學一直是教比較文學的,從柏拉圖講到二十世紀的文學批評,西方的文學理論我很熟悉,但我想給西方讀者介紹純粹的中國文學史。
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翻譯了大量經典詩文,請問您翻譯時,會否參考前人不同的譯本呢?談《紅樓夢》那一節,您特別提及霍克思的譯本,此版本有什麼好處?
張:要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文學,還得用英文作為媒介,因為英文是一種普及的語言。寫中國文學史,如果全是拼音人名、地名,外國讀者恐怕難以卒讀,所以,每講一個作家,我必然要舉上一些作品示例。書裏引用的文本皆由我親手翻譯,因為去找別人的譯本很麻煩,而且涉及版權問題,再者別人的翻譯也不見得好。猶記當年我考北大研究院,專門寫了一篇論文,批評外國人的唐詩翻譯,如何錯漏百出。所以,我對外國漢學家的翻譯向來是很警惕的。哪怕大名鼎鼎的亞瑟.韋利(Arthur Waley),他翻譯《西遊記》裏的「赤腳大仙」,也錯譯成「red foot」,那該是「bare foot」才對。我的書出版以後,獲邀到台灣東吳大學演講,談翻譯。我特意翻出閔福德(John Minford)與劉紹銘合編的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來對照。對比大家都選譯了的作品,我覺得自己的譯文還是稍勝一籌。當然,有的地方是中國文體所特有的,如《楚辭》常見的「兮」字,翻譯時我只好把它犧牲掉。至於律詩講求對仗,那是可以翻譯得像樣的,如我以杜甫的〈登高〉作示例﹕「Boundless forests shed their leaves swirling and rustling down,/ The endless river flows with waves rolling and running near.」(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然而,書裏其他律詩的翻譯,我沒有再緊循對仗的形式,以免外國人讀來,有呆板的感覺。談到《紅樓夢》,霍克思的譯本是極好的。霍克思譯完了以後,把稿子寄給錢鍾書先生審閱。錢先生大為讚賞,寫信給霍:"All other translators of the 'story' found it 'stone,' & left it brick." (Augustus Caesar on the city of Rome: "I found it brick & left it marble."這句話化用了奧古斯都的名言,錢先生把原句的磚塊換成石頭,以切合《紅樓夢》的別名《石頭記》。奇怪的是,霍克思沒有把《紅樓夢》的第一章給完整地譯出來;我引用的那部分就是我自己的翻譯。
世界文學不應再局限於西方文學
李:在總結《紅樓夢》的成就時,您推崇《紅樓夢》足以躋身世界文學經典之列。「世界文學」是一個專門的概念,您認為《紅樓夢》有什麼特別,與世界文學之經典相吻合?
張:我長期研究世界文學史,還跟哈佛大學的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等學者主編《世界文學雜誌》(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深知世界文學在過去某程度上等於西方文學的代名詞。從古希臘的荷馬,到中世紀的但丁,到文藝復興的莎士比亞、歌德,乃至拜倫、濟慈等,皆為非西方的讀者所熟知。但是,一般的西方讀者(甚至大學的文學教授)對中國古典文學幾乎毫無認知,李白、杜甫、蘇東坡對外國人來說,都是陌生的名字。我寫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打破這種不平衡的局面。現在,我們推廣世界文學,就不應再局限於西方文學,還要包括中國文學。再談《紅樓夢》,其技法之嚴密,結構之完整,語言之高妙,遠勝於過往的古典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都是章回小說,結構比較鬆散,有些回目抽出來可以當成獨立的作品,如「林冲夜奔」、「武松打虎」等。而且,《紅樓夢》已翻譯成各國的文字,其中尤以霍克思的英譯本文筆最為優雅,使其流行於英語世界。
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採用了比較文學的視野談中國文學,不時會將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相提並論(如下表所列)。在進行跨文化比較時,您有沒有發現中國有其獨特的文學傳統呢?如海外學術界強調中國文學有抒情的傳統。還有,中國古典文學裏,是否真的沒有史詩式的作品呢?
張:陳世驤、高友工在海外強調中國文學有獨特的抒情傳統,我是不太認同的。中國人看待「詩」這觀念,確實有別於西方,我書裏的第一章已經提到了。西方自亞里士多德以來,便認為詩(文學)是對現實的模仿。但並不能說,西方文學沒有抒情傳統,像古希臘女詩人莎芙的詩、田園詩派(Pastoral Poetry)等作品,都有抒情的意味。中、西方的文學傳統都不是絕對性的。中國的詩觀強調「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是心靈的投射;但是,我們只要看看〈山鬼〉、〈東君〉等作品,便發現裏面也有祭祀功能的,還有很多描述性的場面。再談散文,從《左傳》開始,中國的散文便有很多故事敘述。再到漢賦,裏面很多都是描述的,而非抒情的。所以,過份強調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便會忽略其他的面向。如小說,中國講故事的傳統完全不遜於西方,《三國演義》在元代便已出現了,但十三世紀的西方有什麼小說能與之媲美呢?而且,中國的敘事傳統還能往上追溯,如晉代的《搜神記》、〈桃花源記〉等。
談到史詩(epic),漢族的文學傳統裏的確沒有上千行的敘事詩。我想這跟中文的早熟有關係。中文有極古老的傳統,從甲骨、青銅金文發展下來,不曾中斷。早如《詩經》,主要是靠書寫系統紀錄下來的,而非口頭文學。史詩的產生則主要依賴口述流傳,講故事的人背誦很長很長的詩行,當中會有所重複,而且有不少格式化的處理,甚至有所增補,或即興創作。二十世紀研究口頭文學最著名的學者是米爾曼.巴理(Milman Parry)及其門生阿拔特.洛德(Albert Lord),他們曾到南斯拉夫做田野調查,錄下文盲詩歌吟唱手的長篇詠誦,發現當中有不少的「套語」,並以此推論荷馬史詩的產生過程。柏拉圖的《饗宴篇》裏,也寫到詩歌在被唱頌的過程裏,朗誦者會進行潤飾。《詩經》當然也可以唱頌,像「國風」便是,但我不覺得那算是口頭文學。「國風」沒有長達千行的詩作,更沒有以英雄人物為主題的長詩。
李:在介紹現當代作家時,您不斷指出他們所受到的西方文學影響(如下表所示),您認為有哪些是吸收或轉化是成功的呢?
張:受歐美文學影響,那是五四以後中國文學面臨的一種新趨向。我認為吸收得好的例子還不少的,如朱湘、徐志摩、聞一多的詩,都有過不錯的嘗試,還有余光中,他的西學學養很好。而真正成功的例子也不是全然模仿西方的,像余光中,他的詩裏就有自己的寫法。現當代作家裏,我特別喜愛魯迅,把他的全集都讀了。我尤其喜歡魯迅的雜文與舊詩,但是他的翻譯是完全不能讀的。(李:您寫張愛玲的篇幅遠遠不及魯迅,為什麼呢?)因為魯迅對現當代文學影響很大,所以我給予較多的篇幅。針對二十世紀中期內地那種僵化的文藝觀,夏志清突出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應有的文學地位,我認為很有道理。
未來著述計劃
李:最後回歸中國的學術視野,中文版《中國文學史》汗牛充棟,有哪些您認為特別有參考價值的?
張:用中文寫的《中國文學史》,對我啟發比較大的是袁行霈主編的四卷本《中國文學史》,還有章培恆、駱玉明兩位教授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為什麼是這兩部呢?因為五十到七十年代大陸出版的文學史或學術著作,難免受到左傾的意識形態之影響,我是不能接受的;而上述的兩部文學史是文革以後出版的,和我的看法非常接近。我成長於毛澤東時期的大陸,對於以政治、倫理道德來闡釋中國文學,我是非常反感的。從前讚美杜甫,說他專寫民間疾苦,所以很偉大。但是,中國寫民間疾苦的詩人,又何止杜甫呢?那麼多人寫,為什麼杜甫能夠鶴立雞群呢?因為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啊!
後記:張隆溪教授學貫中西,訪談那天,張教授領我出入古今中外,談了許多的話題,但由於篇幅所限,不可能悉數盡錄。專訪期間,我問張教授,為什麼論《詩經》那部分沒有提及詩六義呢?張教授說,他還會另撰一部英文專著論中國的文學批評史,到時再加以析論。我們熱切期待此書的出版!
(訪問及整理者為本刊特約記者、香港作家聯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