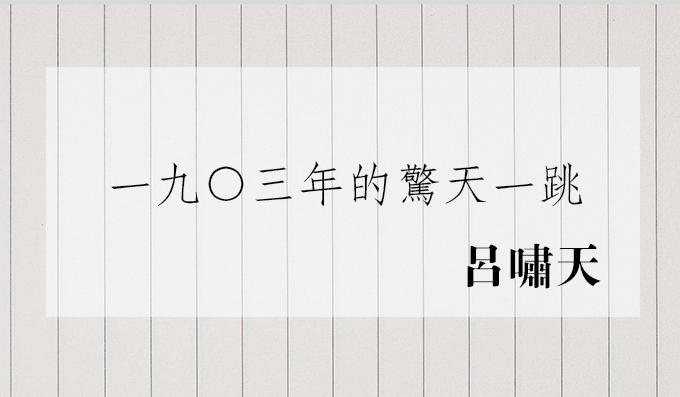附冊:明月灣區
黃昏前的阿拉莫廣場,天空一片灰暗,遠處金門大橋橋樑上的懸索顯得一片扭曲。有和平鴿從天上飛過,我沒有聯想到和平,而是想用槍把牠打下來紅燒了送酒。已在廣場周邊巡邏半天的我感到百無聊賴,只想盡快交班,然後約上約翰、麥斯銳幾個同僚去聯合廣場老街的哈德樂酒吧盡情放縱,然後再借醉逃單吃霸王餐。我叫威史翰,是美國舊金山警察局的一名警察。
我的妻子婭麗是一名醫生,也是一名基督教徒,她長年吃素,每天晚上都要誦讀《聖經》,她臉無表情對我說:「我這是在替你贖罪。」我曾經多次當街毆打手無寸鐵的黑人和婦女,也曾多次借辦案之機把事主的財物佔為己有。
阿拉莫廣場上行人變得稀少,一個身材高大體格魁梧的中年男人在匆匆趕路。一陣風刮過,中年男人的帽子被吹了下來,男人頭上竟散落下一條長長的辮子。
我像發現了怪物一樣又興奮又鄙夷的說了一句:「中國人,黃豬!」
「請你自重,中國人也是人,不容你歧視。」中年男人一邊彎腰把帽子撿了起來,一邊用流利的英語回擊我,他銳利的眼光中有幾分不怒自威的威嚴。
這深深的刺痛了我,我一把揪住他的辮子,一邊朝他臉上搧了一記耳光。中年男人一揮手,我臉上、腹部就接連捱了幾拳。
後來我從《舊金山日報》報道上知道,這個留着長長辮子的中國男人有着不凡的身世。這個男人名叫譚錦鏞,是中國廣東台山人,自幼習武,還苦練英語,期望能報效國家。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他考上武進士,踏實肯幹、兢兢業業,被光緒皇帝重用,成了御前侍衛。一九○三年,譚錦鏞跟隨清國駐美公使梁誠來到美國,成了駐美國公使館外交武官兼翻譯。八月十三日,譚錦鏞受梁誠委派從華盛頓趕往舊金山處理外交事件,當時中國華人在舊金山與當地人發生械鬥事件,他去調查此事。
我叫來了約翰、麥斯銳,準備狠狠的教訓譚錦鏞。但是中國功夫太厲害了,片刻之間,我們三個就被他一人打得趴在地上,我重重的摔倒在地,一顆門牙也磕掉了。我想也不想就吹響了警笛,隨後十幾個同僚趕了過來,看到我們三個受傷倒地,他們一擁而上,拿着警棍朝譚錦鏞往死裏打,嘴裏還吼叫着:「中國人,黃皮豬,打死你。」
劈頭蓋臉一頓暴打後,譚錦鏞遍體鱗傷,躺在地上難以動彈。我心頭還塞滿了怒火,便將奄奄一息的譚錦鏞像拖一隻死狗一樣的拖到金門大橋,拴在橋底,讓行人像在動物園看猩猩一般的「欣賞」這位來自大洋彼岸的中國人。
「我堂堂中華七尺男兒,中國的外交官,卻在這異國他鄉受到如此屈辱?!」
身受重傷的譚錦鏞的內心在滴血,用英語怒罵我和另外的警察。
天黑之後,我和約翰、麥斯銳幾個人合力把譚錦鏞拖上警車,帶回警察局。
到了局裏,他拿出自己的外交官證件,向警長詹姆控訴所遭受的不公與毆打,要求趕緊把他釋放。詹姆還沒表態,我和約翰對着譚錦鏞又是一番毆打,一邊打一邊叫罵:「你是中國人,中國人就應該捱打。」打完之後再把遍體鱗傷的譚錦鏞丟進監獄中。
我和約翰、麥斯銳等收拾一番後還是到哈德樂酒吧喝了個爛醉。第二天上班之後,我和約翰商定等譚錦鏞傷好之後,找個提審的機會,再把他暴打一頓。沒想到的是居住在舊金山唐人街的數百名華人得知梁誠要求舊金山警察局立即釋放譚錦鏞的要求遭拒後,一路遊行來到了警察局抗議。詹姆怕事態擴大,准許保釋把譚錦鏞放了出來。
站在警察局的大門口,譚錦鏞指着警長詹姆說:「我是外交官,你要向我道歉。」
「做夢吧。」詹姆很不屑地說。「在我眼裏你就是黃皮豬、東亞病夫。」
一位上了年紀的華人把譚錦鏞拉了過去,流着淚勸說道:「兄弟忍忍吧,國家貧弱無能,咱們飄洋過海的華人哪個沒受過欺侮?世道就是這樣,沒有辦法。」
眾人離開之後,來到金門大橋橋面上的譚錦鏞,望着橋下波濤洶湧的海水痛心疾首地說:「我一個國家的外交官,遭到如此的欺凌羞辱,個人尊嚴何在?國家尊嚴何在?」仰天長嘆一聲後,他縱身一躍,跳入水中以死明志。
舊金山的許多報紙報道了這一駭人聽聞的外交官事件。正在美國訪問的梁啟超氣憤不已,怒吼:「堂堂中國,受此侮辱,天理何容!」並寫詩悼念:「丈夫可死不可辱,想見同胞尚武魂。只惜轟轟好男子,不教流血到櫻門。國權墜落嘆何及,來日方長亦可哀。變到沙蟲已天幸,驚心還有劫餘灰。」
直到這個時候,我才知道中國人血性和尊嚴能爆發驚天動地的力量。作為事件的罪魁禍首,我感到了深深的害怕。後來警局找了個理由,把我開除了。我天天躲在家裏。婭麗已跟我離了婚,帶着兩個孩子走了,家裏只剩我一人。她留給我唯一的禮物是一本《聖經》,和她摘抄的兩句話:「罪的快樂,只是一時,它的痛苦卻是永遠。血除去了我們諸般的罪,而十字架卻打擊我們能犯罪的根源。」
後來,我在一家教堂裏做了一名牧師。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佛山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佛山南海區作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