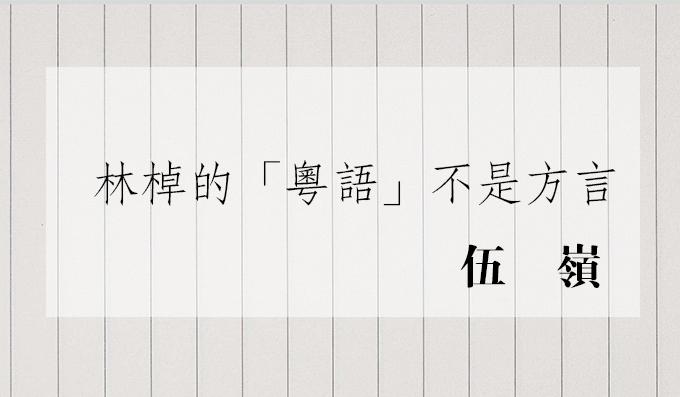附冊:明月灣區
林棹的文學是不能輕易被分類的,無論文學界如何分析她、評論她,她只管在曠野上奔跑就對了。
出道至今,林棹的兩部作品《流溪》與《潮汐圖》皆獲文學界的青睞,什麼「新南方寫作」與「女性作家」的標籤統統可以撕掉,她在其他作家的眼裏被視為一位「重要的作家」,其作品被視為「重要的小說文體」。出生於深圳的林棹,無疑是近年來南方文學的代表。
在成為職業作家之前,林棹就是一位普通的打工人,她從事過遊戲設計,賣過花也種過樹,就連林棹這個名字也是「虛構」的,按她自己的說法,其原名用普通話念起來像某種素食,用粵語念起來像某種肉食。總之是食物。所以她不願公開提自己的原名,她用虛構的名字將自己和世界隔着一些距離,而且,她覺得「林」的意象挺好。這大概與她種過樹的經歷相關吧,雙木成林,林棹已在自己的「兩棵大樹」下收穫了應有的文學夢想,她正在種下另一棵—用詞語製造困境,又用語語突圍的文學世界。
《流溪》和《潮汐圖》兩部作品的主要場景都在珠三角區域,用了大量的粵語寫作,以致作家林白稱其「語言新鮮、繁茂,音調特別,是粵語獨有的鏗鏘」,且「有強烈的詩性」。
在此,我想簡單說一說她的「粵語」與她文學的關係。
林棹深知廣東人的幽默感、實用,不拘泥於形式和觀念的特點。「比如《潮汐圖》裏的商販,眼界寬了,心態就輕鬆。」她覺得廣東沿海就是這樣的氛圍,信息從四面八方來、很多元,不是單一路徑、單一成份。
這大概是粵語地區的特點,雖然在故事之外沒有方言,但粵語文化隨處可見。比如寫到沙面時,林棹提及的勝利賓館就有些來歷。賓館前身是一八八八年所建沙面酒店,後來改建為域多厘新酒店。「域多厘」,是粵語音譯的「勝利」。所以,身為作家,林棹開始關心歷史,不僅是關心粵語這種方言,而是將方言代入進相關舊事,而許多往事又是基於四面八方的背景,這些都與外部世界發生關係,包括粵語。
很小的時候,林棹就清晰地認識到,身處多方言環境下會對許多事物有所感知。她在一次訪談中說,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她就讀的小學裏,上課的老師來自五湖四海,有着各種各樣的口音。不同方言和它們所代表的或強勢、或弱勢的地域會成為一種隱秘的壓力施加給孩子。這種經驗可能是多方言或多語言地區的孩子們共有的。在特定環境下,選擇哪種方言,以及選擇背後的動機,是很值得考察的。後來,她把這種體驗寫進了《流溪》裏。
而她的敏感,與對詞語的在意,還在於粵語在她生活中的變化。她上中學的時候,在學校叫茶餐廳的外賣,會叫到「芝士焗雞」。後來年月漸變,她發現「芝士」變成「奶酪」,「忌廉」變成「奶油」,「多士」變成「吐司」。直到寫《潮汐圖》時,她找到幾種十九世紀粵英、粵葡詞典,才得以看見詞與物之間互聯、失聯的微妙歷程。這個問題對很多人來說不重要,但她覺得和自己關係密切,因為它關涉着故人、她生活過的街坊市井和回憶。
有的人認為,林棹用粵語寫作會給讀者帶來閱讀上的障礙,其實不僅沒有障礙,在粵語高頻出現的《潮汐圖》裏,許多讀者都為巨蛙(書中主角)而共情,為生離死別而落淚。
在林棹的文學裏,粵語自然是方言的運用,要使用當地的聲音才能讓讀者代入當地的故事。但粵語在林棹的詞語裏又不是方言,它是一種文學性的音調,讓文本更加繁茂。
(作者為《深港書評》主編、文化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