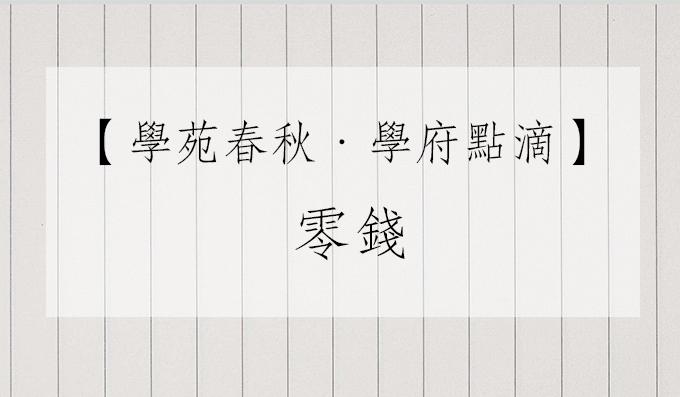學苑春秋
依舊在生活中的它
暨南大學文學院 王燕婕
是選擇被零錢裝滿的錢包?還是選擇一部手機或是一張卡?我想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後者。事物都具有兩面性,電子支付的廣泛應用為社會節省了大量的生產資源和管理成本,同時它卻遺忘了那些跟不上時代發展的人。我的父親習慣用零錢和八達通作為日常的支付工具,每每教他如何使用這些手機應用程序的時候,他總是一臉似懂非懂,然後不耐煩地打斷了我的教學。「雁過不留痕」,父親依舊實行「一卡一現」,我的教學註定是失敗的。
我並非拒絕使用傳統貨幣,與此相反,我很喜歡攢硬幣。我的家人都會特意將身上的零錢都留給我,但是母親還是不太理解為何我在這方面比他們還要「古董」,畢竟硬幣有諸多缺點:一是重,二是不便攜帶。傳統貨幣對我來說是生活的具象化,我很喜歡硬幣在投幣機裏橫衝直撞而發出叮叮噹噹的響聲,它不是冰冷的虛擬數字,也不是冷漠的電子聲,它是我逃離手機,回歸現實的「提示音」。傳統貨幣承載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記憶,它是父母向我們表達愛意的方式中最直接的形式,也是我們最初認識這個社會基本生存準則的重要媒介。或許在未來的某一天,貨幣失去了它的應用價值而飛入櫥窗。在此之前,零錢在我們手機失靈的時候還是發揮着重大作用。
神沙
香港浸會大學 陳羿衡
一枚手指大小的硬幣,雖然與神無關,卻如很多東西,渺小但無處不在,甚至有着非一般的神力—向上拋,可以決定一場賽事;向下放,可以體現一份尊重;向外遞,可以給予一份鼓勵;向內塞,可以驅散邪靈。⋯
然而,現在要談到會因外出沒帶散銀而氣結的原因,大概只有幾個:有優惠卡要刮—要說的話,好像也不成幾,也許還有體驗新科技吧。有次路過銅鑼灣Fashion Walk,多了部「神沙機」,起初還以為是內裏藏着個街頭霸王那種,後來看着「將你的散銀變成……」一句,我想,存入帳戶,帳戶有多重,也不能放在口袋,不說,存入的是什麼,根本無人知曉,就如那頭豬。
與尋常家相若,成長時總有頭豬,吃掉神沙,瞧着它吐出份玩具來。爺爺總說,未雨綢繆,每晚把他買麵包剩下的兩蚊、買菜剩下的五蚊,交給我餵飽豬。後來豬撐死了,但當時並未需敲出零碎的愛,卻不知放在哪裏。爺爺仙遊後,他只留下張數天前壽辰給我「買玩具」的一百元,我安放在錢包內,用優惠卡隔開,至今仍記得它的編號。我偏有次匆忙下,把它花掉,為此鬱了半年。
直至我有晚輾轉反側時,撞起枕下有包神沙。
零錢的重量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賴文龍
從前的快樂總是「廉價」與「簡單」的。
在我十歲前,父母因工作原因分隔兩地,我更多的時候是與父親一起生活。父親身兼母職,時常接送我上學,但我與他之間的對話和活動並不多,回憶中只有在回家路上閒逛雜貨店的光景最為清晰。他總會給我一點零錢,好讓我買一些小零食或者玩玩店裏的「乒乓波機」,那是我每天最期待的時刻,現在回想起來,那時手裏緊握的零錢,莫名地多了幾分重量。後來我升讀鄰區的中學,經常要「搭紅Van」,父母就總會把裝滿零錢的小布袋塞進我書包,可是零錢既重又不方便,走路時還會錚錚作響,偶爾我還故意取出錢包扔到桌上,瀟灑出門。有時上到小巴,才知瀟灑的代價,都是自作自受。可知拿出「大紙」給司機找零,總會惹來髒話和揶揄,倘若碰上司機心情不好,還會引來痛罵和詛咒,耽誤其他乘客的行程。幸好有幾次,某些頭座乘客看出我的窘況,竟然仗義伸出援手,幫我多付幾個零錢,面對這些善意的陌生人,我只能連聲道謝,鞠躬道別,尷尬難堪地伏竄到衣領去。小小的零錢,原來都是擲地有聲,情味斐然。現在電子支付的普及,孩子只知「嘟」聲消費扣數,甚至從未使用過零錢硬幣。隨着零錢被淘汰的將來,生活的質感會否也逐漸散去,變得愈來愈虛無,而我們還能抓緊多少回憶的重量呢?
零錢太多
香港浸會大學 黃奕奕
「我的零錢太多了,先幫我用掉吧!」
記得在孩童時期,我和夥伴相約去家附近的文具店買畫筆,在路上經過一間小食檔。新鮮出爐的雞蛋仔散發的蛋香瀰漫了整條小巷,我們對着烤得金黃的雞蛋仔邁不開腳,都想嘗嘗它的滋味。
我的手裏揣着媽媽給的二十元,身上也沒有多餘的閒錢,於是我在心裏告訴自己還是買文具比較重要。夥伴在旁邊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特意向我搖了搖他的背包說:「我帶了很多零錢,每天裝在包裏實在太重了,先幫我減輕一下負擔吧!」當我還在猶豫的時候,他又說:「大不了下次就換你付。」後來我才漸漸曉得,他分明不是零錢太多,而是想要不着痕跡地對我釋出暖心的善意。
如今,我在家中也放着一個偌大的玻璃罐,裏面裝滿了我平時出門特意存下的零錢,而我也養成了身上隨時放一點零錢的習慣。在路上看見誰拿着零錢捐款箱,還是周末遇到賣旗活動,我都會自然地走過去把身上的零錢捐給他們。因為我知道,它們看似無足輕重,有時卻有很大用處。不過是舉手之勞的事,何樂而不為呢?
零錢對很多人來說或許是一種煩惱,但對我而言,它卻是一股源源不絕的暖流,把我從他人身上收穫的善意繼續湧向更多有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