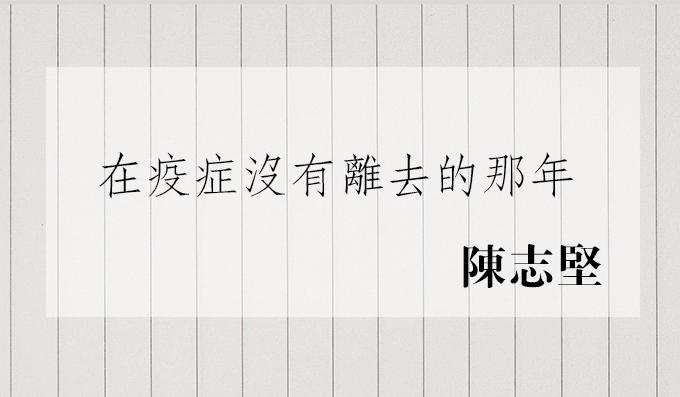文學.藝術
起風了,已忘記了曾經那種祥和的感覺是怎樣停駐在內心。
我們都被困在內室,宅居在家,疫症似乎沒有平息的跡象,城市被慌亂佔據,關係受空氣所傷,四圍都是驚恐。死亡的道路一下子暢順,在毫無預兆下,認識和不認識的人不自覺地列隊進入,也無法說什麼遺言,反正註定孤身上路。人瞬間化為一堆數字,除了囓咬着時間,也只能寄託於淚痕。
雙照淚痕乾,想起曾經虛幌半掩,在明月下看清風、聽月色映在水上靜默無聲。那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時維九月,序屬三秋,如果不是時間過渡得太快,我還以為自己很年輕。不是嗎?這個和那個身邊人還不是好端端地活着,如常地上茶樓、逛書店,如果他們沒有老,我也在平行時空內繼續任我行,因為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直至疫症,才曉得死亡是如此真實和決絕。那天和友人到九龍塘又一居與醫生朋友見面,趙孟準醫生以詩歌譜寫神的樂章,除了在歌詞中呈現神的慈愛,也說明自己如何親眼看見神。〈神!祢在掌管〉,掌管時間,掌管萬有和空間,可是,就這次相見以後,沒料到生離成了永訣,在還未來得及道別之際,也就只能在詩歌中回想生命的本義。於是,我再次思考年輕的價值,因為年輕和年紀本不是同義的詞。
年輕的揮霍與代價
年輕可以揮霍,隨便溜日子,無聊時滑手機,有的是時間。對於死亡來說,年輕是最有力的對抗,性格不必怎樣講究,某段關係沒了可重新再有,做事不着意細節,因為年輕,世界也不用對我們太過認真。然而,這不是真正領略年輕的快樂,因為真正快樂的年輕要深刻體會。那是怎樣的體會?在疫症未流行之前,我曾經揹起背包走在風中,遇上陌生的客旅,路上談,說什麼都可以。那是一次絕密之旅,時間在耳邊盤旋,巴黎巷弄轉角的小攤,賣畫的婦人端坐在地氈上,花白長髮束起,深邃的眼窩,雙手交疊在膝前,消逝的女人感到青春,那持續地重整又隨性的身體,是街頭上最曼妙的身影,而四周掉落在地的黃葉,不像瞬逝,乃是一次生命的重組,在花街的樂韻中起舞。於是,我終於明白,年輕的美麗是如何當一個沒有羈絆的客旅,在寧靜的遠洋沒有默念自己的方向,在遙遠的他方沒有等待自己的彼岸,活在無以名狀的空氣裏,想像落葉長出新芽的美好,而光影亦尋常地照着臉靨。
後來,周圍開始有了雜音,聲音如乾裂的春雷,提醒年輕的代價。於是,一夜之間年輕成了失焦的代名詞,所有意志低沉和意識掠奪都歸咎於過份年輕。我們被提示急速成長的必要,成長之於年紀的速度,能超越多少就多少,不再像閒散的畫家,一如黑稠夜空中閃現的流星。年輕人一再聽見別人替自己規劃好的人生,人人手捧水晶球預告未來的榮耀,而只有自己沒有。終於,厭倦聲音如厭倦熟悉的位置,我們離開眾說紛紜的地方,又脫去別人的嘉許,在別人無法進入的時程中,替自己編織餘生。不是世界強迫所致,而是我們認為自己需要負上一些責任,且不經意地已在責任大道上行進。責任就如泥盆旁邊的花屍,死了會再活過來,且天天向我們討債。然而,我們自是樂意的,因為責任一旦變成野心的濫觴,便會至死拼命地以血肉鋪路。有一位年輕有成的學生,畢業後旋即創業,做汽車銷售生意,怎料汽車生態一轉自然困難重重,學生曾經費盡心思替這壯年人生路命名,路旁房子鋪設簷篷以敵擋強風,可是風向轉易,一下子卻變成無主孤魂,如落危途。幸得後來靈魂意志被喚醒,才重新創造了新的將來。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有這種意志,千錘百鍊後一蹶不振,除非我們有預先讀懂自己。
留住年輕
只要相信必定成功,有能釀出生活的芬芳,人也醺醺然。日子就在責任大道上如此隨流失去,到能夠意識過來時,原來已勞碌半生。才想起半生以來費盡心計,結果什麼也得不到,在奮鬥中失落,在人事中周旋,到頭來只換來一身衰弱,以身體賺取錢財,以錢財醫治身體。直至夜闌人靜之時,才真箇意識到,原來年老色衰的日子早已不遠了。步履蹣跚走在小道上,膝頭疼痛,走幾步路也絕不容易。以前重視外觀,燙髮美肌,天天受人關注。如今也顧不得衣履穿搭,反正一頭銀髮,手挽着兩個黃色塑膠袋,一手一個,但求想盡辦法把小店購來的生活必須品帶回家裏,我們還要替自己洗澡、晾衣,也要煮吃、洗碗,餘生獨自過着不輕易外出的蟄居生活。只是,我們刻意偽裝看不見道旁,原來道旁的簷篷早已拆卸,不知何人在欄杆上掛上許願竹,預表祝福,祈求祥瑞,才想起自己已落入長命百歲的祝願裏,在鄰人討論多多關照的名單中,已經有了自己的份兒。更不願意起風,風吹奏許願竹詭譎的迴聲,使我們想起年少和壯年時,更想起許多年前那個巴黎巷弄轉角賣畫的婦人,她竟年老得如此優雅,年老得如年輕的自己。於是,心頭猛地給戳了一下,曾經以為自己年輕得豪邁,在尚有大半生的年華裏,青春可無限地揮霍,青春就如站在巖石上縱身躍入海裏的少年,而幽坐在白沙灘上的老人正觀看着這少年人美妙之姿,只是,當老人看見精壯少年的舉措後,才驚覺自己已近垂暮,回首從前只留下多少不願再想起的事端,而當初卻費盡心思經營,如今看來只是一陣隨時飄散的雲霧。青春一夜就變老,我們一直以為自己是巖石上的少年,豈不知道無論在什麼年紀根本沒年輕過,終於醒覺,才曉得多少悔恨可把我們剩餘無多的年日無情地折騰。
於是,我們會問,到底應怎樣經過一生?人生只有一次,春光韶華易逝,不是什麼都可以留得住,也不是什麼也留不住,若然要留,應該留什麼?那請留住年輕。年輕從來不是年輕人的專屬,年輕在每一個人心間,只消喚醒年輕的靈魂。不是嗎?年紀雖大,沒有年輕的體魄,但我們仍然有年輕的靈魂。早前聽說荷蘭一位七十歲的老婦人跑了一趟半馬拉松,她在四十六歲時開始跑,直到現在,來到七十古稀之年,終於挑戰全馬拉松了,我不知道她能否完成四十二公里有多的路程,但我知道年輕的魂在她裏面,這種重新遇上的年輕,有如重逢甘雨。這是疫症沒有離去的那年,因病離世的沒有分健壯還是體弱,生命長短沒有人能說得準,但生命的溫度人人可以調校,濕氣太重,四圍冒出黴菌,整個思想系統就如癱瘓了一樣,什麼也不接受,如遇上潮濕的氣候,宅居在家,反正如病懨懨的廢棄住宅一樣。事實上,這世界沒有靈丹妙藥,但有寧神養氣的靈茶,提神醒腦,讓我們想起從前的靈動和巧思,至今根本還在,沒所謂不好意思。老年得子不是人人都有,或者人人想有,但老年得「輕」卻是絕妙的年華,既然蘇州過後無艇搭,倒不如想像自己如何年輕,幹一番新的事業。問題在於身體是否能夠負荷?不是人人都能應付馬拉松,有時走幾步路也感氣促。然而,有人衝浪,有人滑水,有人暢泳,有人浸腳,那又何干?只在乎是否落入水裏,感受水的冰涼,傳至腦海而形成清新和舒徐的愉悅?還是我們只想起腳板下的幼沙,在沾水後竟怎樣黏着腳板,為免煩擾,索性不沾水半分,想來想去,倒不如穿上鞋子,生怕老年風濕又發作了。其實沒所謂沾不沾腳,反而每當我們因年紀而不做某件事時,正正就是思想是否應立即做起這件事的時候了。
死亡那又新又真的意義
每一天,接近死亡又近一日,人死後被埋葬,或肉體被焚燒,然而死是無可避免的,我們什麼時候開始擔憂被泥土沾染?什麼時候開始掛慮被野火焚燒?死亡預告,年輕時不覺,在日夜顛倒的繁忙事業裏我們更加不覺,且相信和慶幸只要努力地拚事業就能釋除憂慮。直至一天身體異變,又被四周圍充滿可怕的事物弄得體無完膚,生活的呼告無效,於是揮之不去的夢魘佔據思潮,像倒數的年輪,一天一天地算計剩餘的日子。死亡成了最有力的控訴,才想起大半生以來原來對不起不少替我們準備安樂茶飯的親人,對不起不少曾經出死入生的夥伴,於是,死亡成了重要的議題,來不及補償,來不及挽回,重新上路這種年輕的意義盡失,因為死亡本來就是終結,且沒有回頭路。然而,回頭路沒有,但來時路卻是有的,只要認清我們來自哪裏,就會曉得死後到哪裏去,如果世界的創造來自造物主,死後就會回到造物主那裏去。《聖經》說:「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你們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十三節)死亡的可怕在於其代表了一切的終結,除非我們深刻地理解原來死亡那又新又真的意義,在念念不忘的瞬間,在一息尚存之前,我們仍然可以享受年輕。
其實也不在於回不了頭,最恐怕是已來不及。村上春樹說,我們一直以為人是慢慢變老的,其實不是,人是一瞬間變老的。原來,在生命燃燒的日子裏,那迎向死亡的道路上,冥冥中已有人為我們縫製壽衣,特朗斯特羅默如是說。於是,一場無情的疫病終結了諸般情愛,留下來的人有沒認真對待每次秋晴和春分?既然生命有着隨時中斷的哀情,那麼,我們更應真實地體會年輕的意義,青春不留白,如朝着天燈向澄明的天空飛去,在仍然祥和的日子,思想死亡是怎樣無聲地靠近,和那回復年輕的奧秘。
(作者為大學客席講師、中學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