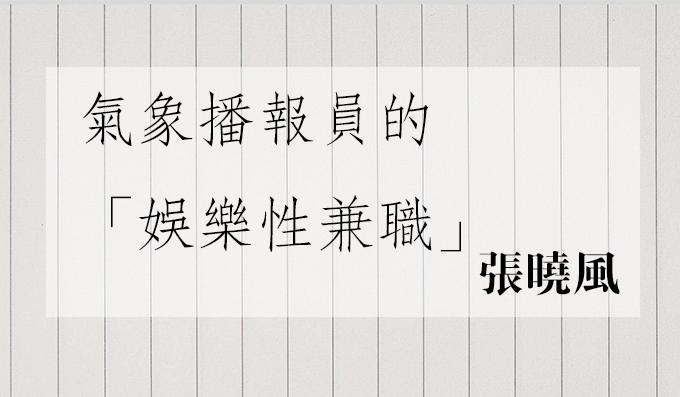心田集
我跟丈夫退休前都在學校教書,我的學校距家十一公里,他的則離家四十二點二公里,我自己開車去,他搭的是校車。
也不知是不是為了「遠」這個原因,他出門前常常不安:
「不知道今天下不下雨,不知道天氣會不會轉熱,不知道……。」
我們教學的鐘點都算多,大約十小時,偶然也會開成十二小時。這個時數一周去兩天應該也就可以完成義務了,但學校方面卻要求每周最少要去四天,以便學生要找老師請教的時候,有八成機會可以找到。
所以,我家那口子,每周大概至少有四次會把那奇怪的有關天氣的「天問」在我面前叨個沒完沒了。
「喂,你搞清楚,我不姓『上』,我的名字也不叫『帝』,刮風下雨不歸我管啦……。」
「上個禮拜三,氣象播報明明說天氣會轉涼,結果,我穿了很多,哼,後來一件件脫,弄得抱在手裏不知怎麼辦……。」
「哈,總比說天很熱,卻忽然轉涼了,結果凍出感冒來好吧!」
「你還笑,你都沒有同情心……。」
「我教過你方法了,你不聽,你書包裏應該放個大袋子,很輕很薄很韌的那種,撐開來有兩個A3紙大,收起來只有拳頭大。有了這種袋子,什麼東西都不怕,都可往裏塞,都可以輕便拎起……。」
「別說那麼多,我現在急着去趕車……。」
我知道他真正的意思是:
「你快點給我拿個主意……。」
哼,我才不上當(因為已經上過太多次當了),到時候他會說:
「你看,你看,我聽你的話,沒帶傘,結果淋得一身濕……。」
噫!「唯男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用君之心,行君之事,老婆我,誠不知天象!」
至於我自己,因為駕着一輛「迷你型小型汽車」,就彷彿有了「隨身小屋」,那裏面有傘、有外套、有水、有餅乾、有紙、有筆,就算碰到嚴重的惡性塞車,我也能立刻抽出一本《唐詩》來,把小車一轉眼變幻成古代書房。哪怕只讀了一首詩,也覺十分划得來。
不過,我雖不在乎天氣,出門時也難免想看一眼天色,這大概是出於人類古老的潛意識吧!
一般而言,我頗能預測天氣─但,只限於春天。
春天怎麼啦?春天,我的陽台上有一種不請自來、名叫「酢漿草」的小野花,它們的花小小的,只指尖大,粉紅色,花期是三月初到五月半。如果我早晨九時出門,它們的花是打開的,那,這一天就是晴天了。
有時它七時半就開,但到了九點,想想又後悔了,竟又閉了─那麼,那天很可能會下雨……。
過了春天,這花消失,我的觀測對象沒有了,我也就無從占算天氣了。
記得我有一次到台北郊區木柵,去看一家木板建材行,那裏人車比較少。我看完貨,走出大門,忽然看到這家商店門口有棵三人高的青翠的行道樹,於是停下腳來。我不是受那棵樹的吸引,吸引我的是樹下的一叢小野花,粉紅色的酢漿草。路旁有行道樹不稀奇,但樹長得那麼挺拔秀氣很難得。再加上樹下居然又開着六七朵小野花,更是極為難得(台北市區的行道樹下就開不出小野花來)。我忍不住大叫了一聲:
「哎呀!太好了,今天要轉晴天了!」
店員聽我一叫,連忙跑了出來:
「什麼?什麼?」
「天要晴啦!」
「你怎麼知道?剛才還在下雨呢!」
「哎,這,你就不懂了,你看見嗎?這種樹下粉紅色的小野花,不怎麼起眼。可是,它如果開了,特別是在早晨九點之後,這一天,就不會下雨了!」
「真的嗎?為什麼?」
「你想,花為什麼要開?它開花並不是要給我們人類來欣賞的,它是為了招蜂引蝶啊!它需要有傢伙去幫忙它播粉啊!」
「所以呢?」
「所以它要計算得好好的,必須選個好晴天才來開花,這樣,蜂蝶才會來採花粉─如果它下雨天開花,那就慘了,它的粉很快會讓雨水沖跑,那,它就結不成籽,它就沒有明年的春花了!它就『絕後』了!」
「咦?它這麼小小一棵草,竟有這麼聰明的算計?」
「對,它的命只有短短一個春天,就沒了。而且,它們不用上學,它們生來就知道,知道下一刻是會出太陽還是會下雨。」
「我們的氣象播報員,讀了那麼多書,卻老是把氣象播錯……。」
「唉,你不知道嗎?氣象播報員都有個兼差─他們的兼差是負責『撒謊』,目的嘛,是想『娛樂』我們一下啦!」
今年(二○二三)四月我去廣西簽書,出版社問我除了桂林還想去哪個城市,我毫不思索地就在電話裏叫出來:
「柳州!」
那是我七十五年前逃難途中的城市!
到了柳州,當地的人帶我去看柳公祠,在大大的院子裏,我又看到幼年時代的大片春日酢漿草了。
「酸咪咪!」有個陪我去的女孩雀躍大叫。
「你們叫它『酸咪咪』嗎?」
「我們大家從小就都這麼叫的呀!」
哦!對了,想起來了,我小時候,在柳州,也是這麼叫它的──小時候,七歲,在柳州香山國小,同學都喜歡咂它的味道。
一株小草,其間有多少造化的恩惠和神奇啊!它才是最準確的氣象播報員,從不撒謊。
而我,是那個無意中窺見「天庭機密」的人。
(作者為台灣著名作家、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