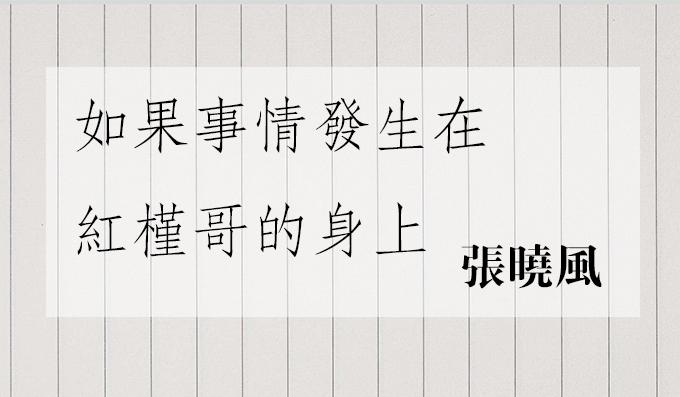心田集
古時候,在中國,女人不太有正式名字。
百分之百沒名字嗎?也不是,大概沒名字的佔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吧!
但,所謂有名字,往往也只是「姜氏」什麼的,等於沒有。
為什麼沒名字?因為─唉,根本不需要呀!女孩要名字幹麼?等長大了,嫁給「二楞子」,不就自自然然撿到現成的「二楞嫂」這個名字了嗎?等生了兒子, 也許又變成「小狗子他娘」。等死了,把丈夫的姓加爸爸的姓寫成「王母李太夫人」就行了。所以,幹麼要多費一道麻煩, 來為女兒取個名字?
但民國成立了,一九一二年以後,有點不同了。我外公為兒子和女兒都取了有「慶」字排行的名字。而我父親也為長女取了個有一點男性化的名字,叫乘風。但依當時風俗,女孩在家好像另外還得有個小名。
我算次女,三歲以前,大家叫我「妹妹」。母親是父親元配死後在一九四○年結婚的續絃妻,因為戰爭,他們早期的生活一直在旅途上。
一九四四年媽媽又生了妹妹,於是我立刻升級為姊姊,我的名字必須改了。學名反正是一出生就取了,此刻,曉風這名字於是正式啟用,哈!也就是說,民國三十三年,我改了年號。幸好生的是妹妹,如果生的是弟弟,我這「妹妹」的年號就會一直沿用下去。
母親又慎重其事地把三歲的我叫到她面前,跟我說:
「你們張家的排行是『家風振德……』, 你爸是『家』字輩, 你是『風』字輩,但女孩在家裏另有個小名, 你的小名叫白槿,就是白色的槿花的意思……。」
白色我懂,槿花我剛好也懂,因為當時家中牆外就有一棵。但白槿二字,三歲的我不喜歡:
「為什麼要叫白槿?我喜歡紅槿!」
「唉,」母親嘆了一口氣,她自己一向喜歡紅色,「我也覺得紅槿好,只可惜, 這名字給你堂姊取去了。」
「堂姊」,這名詞我就不懂了─逃難的小孩從來不知道什麼親戚。據說她比我大十幾歲,我生晚了,好名字給人搶先佔了。我有點生氣有點嫉妒,卻也無可奈何,一個家裏總不能有兩朵叫紅槿的女孩吧!
後來,我其實從來沒機會見到這位堂姊,原因之一是戰爭,原因之二是她在青春正盛時就死了─我猜,她大概只活了二十年吧!
她一直住鄉下,而我八歲以前一直在逃難途中,雖然身為小孩,卻也忙得很,例如到不同的省分去讀不同的學校, 要適應不同的老師,並和不同的同學交往……。
一九四九年以後,我終於「定居台灣」了。
大姊乘風跟我同住在一個屋頂下,她比我大十六歲,日本式的屋子,房間與房間之間是通行無阻的,有時候她也會講故事給我聽。其實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 一九四六年,我們由重慶遷到南京,她已搬來跟我們同住。但她那時大半時間「住校」讀書,周末才回家,所以見面時間不多。一九四九到台北,她好像不讀書了, 準備着要把自己嫁掉,日子過得挺悠閒。
紅槿的死, 我是那時候才聽她說的……。
「那時候啊,仗一直打,答答(徐州方言說「爸爸」的意思)人不在老家,家裏吃的也不夠,用的也不夠,徐州是『淪陷區』,錢也匯不過來,日子真是過不下去了……。」
鄉下人,開口找人借錢是很難啟齒的,但如果去找親戚「借點糧食」倒在情理之中。我外婆家因為是大地主,存糧頗多,那時因外公已在戰爭中捐軀,家中孩子也多散在各地,外婆是女強人,她獨力一人持家。
有親家來借糧,好哇,外婆說,存糧多的是,說一聲,隨時叫車子來拉就成了。而我們張家這邊當時負責接洽借糧並主持運輸,乃至賣掉一部分糧食轉為現金去使用的「辦事員」是紅槿我那位堂姊。我猜,可能家中雖有男人,但都拉不下臉來做這件事,我爺爺窮雖窮,卻自視甚高,大概抵死不肯去跟親家母低聲下氣, 任務於是落在孫女紅槿身上。外婆看到「曉風我那外孫女的堂姊」來了,也熱心款待。我是外婆唯一照顧過的外孫女,因她那時年輕,才五十出頭,為了給母親「做個好月子」,她坐鎮指揮,每天熱心督促傭人殺一隻老母雞燉湯,強迫我媽媽全吃下去。母親奶水因而豐沛,我也受惠。我滿了月,她才放心回徐州老家。
借米成功,父親老家的情況立刻有了改善。但,紅槿也變了,她忽然買了許多漂亮的布並做了新衣服(那時代不太有人賣「成衣」),手上也多了些錢。她甚至交了一堆男朋友,晚上還出去玩。她並不是「職業婦女」,她的錢哪裏來的?是「過手三分油」的「自肥案」嗎?打扮妖冶,招蜂引蝶,族中的人認為實在是敗壞家聲。有天晚上,爺爺看不下去,便把她叫去痛罵了一頓。
我爺爺脾氣大,罵起人來有氣勢、有辭藻、有聲量,誰也不是他的對手。紅槿也不回嘴,當時其他家人也沒誰敢開口勸一下。
紅槿或者有罪,她或者侵佔了因賣糧而到手的公款,否則那些「治裝費」是誰付的?而那時代大家庭大約二十人住一起,訾罵之聲,人人都聽到了─她第二天怎麼做人呢?
此事不勞大家煩惱,第二天一早,大家發現她死了。一根繩子,她了結了自己。
她的母親嚎啕大哭,大着膽子去痛罵爺爺,認為紅槿是他逼死的。紅槿就算有罪,其罪也不及於死,為什麼要把她往死裏逼?
聽大姊的敘述,爺爺最氣的不是「貪污案」,似乎是「風化案」。她不該在小鎮大街上公開跟男人吃喝玩樂。這件事, 後來在家族中是件不能提的禁忌。
我從未見過紅槿姊,連照片也沒見過,但想起曾有個暗夜,她趁更深無人時(也許穿著她新做的漂亮衣裳),自去爬高懸繩、自去套頭、自用腳踢倒凳子的一連串動作,心裏還是有惻惻的憐痛和哀傷。
唉,如果她不是紅槿姊,而是紅槿哥,爺爺大概就沒那麼憤怒要去「維護家聲」,那個晚上的可怕情節,大概就不會上演了吧?
( 作者為台灣著名作家、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