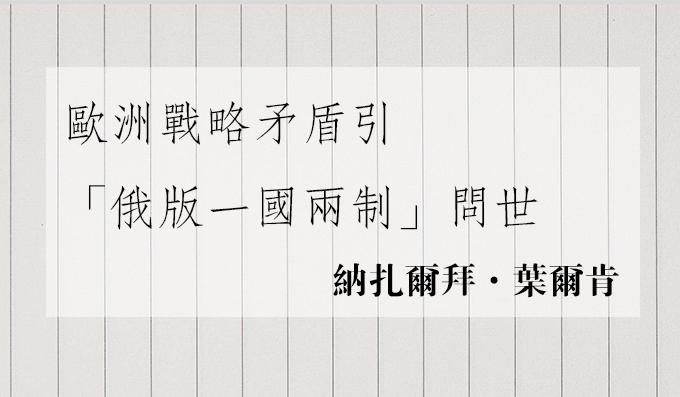社會.時事
眾所周知,突發於今年六月二十三日的所謂「瓦格納叛變」事件,在其所屬「集團發言人」葉夫根尼.普里戈任公開發表一系列「反政府言論」後,伴隨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京發表深夜緊急「五分鐘講話」,以及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所倡導的「第三方斡旋」保證下,僅在短短一天時間內得以迅速「平息」,致使各國媒體在極為短暫的二十四小時內不可避免地遭受源自克里姆林宮的「閉門羹」,進而將其普遍錯誤地視之為戰時所應當發生的「諸侯叛亂」,而非醞釀已久的「內部清洗」。
無足輕重的瓦格納集團
反觀此次俄國境內所發生的閃電式「一日危機」,不難看出瓦格納軍事集團既非俄國史上家喻戶曉的反專制革命派十二月黨人(Decembrists),也非歐陸史上臭名昭著的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勞工黨(即納粹黨)之「左膀右臂」,即被德意志第三帝國國防軍視之為眼中刺的衝鋒隊(Sturmabteilung)。究其原因,瓦格納軍事集團首先並非是由上層精英所構成的正規高等軍官團,且從未被西歐主流文化所薰陶,其所屬世界觀與自我認同無法與一八一四年長驅直入歐洲腹地、戰勝拿破崙並入主巴黎的十二月黨人相提並論,乃名副其實的編外「烏合之眾」,毫無法統或道統可言。
除此之外,擁有「編外自己人」特殊地位與身份的瓦格納軍事集團,作為蘇聯解體後用於專收其體制外具有強力部門背景人員的「臨時據點」,在俄國現有之權力平衡與體制框架中可謂無足輕重,既不是現任總統普京起家所借之「御用暗器」,也不是當前俄羅斯執政黨(即統一俄羅斯黨)立足所需之「堅實根基」,更不是能夠與俄羅斯國防部及各克格勃系安全部門可單獨或一併分庭抗禮的「組織機構」。
與之相比,瓦格納軍事集團所屬「集團發言人」普里戈任則是更加名不見經傳的棋子型人物,是克里姆林宮自蘇聯解體以來所有意扶持塑造的眾多臨時性配角之一,必要時既可高高舉起也可輕輕放下,乃名副其實的戰時「馬前卒」和戰後「犧牲品」。歸根究底,普里戈任自始至終都不是一個願意為俄國民主事業赴湯蹈火的英雄人物,相反則是為捍衛俄國帝業不惜手足相殘與禍害蒼生的「馬前卒」。除此之外,普里戈任從未躋身步入克里姆林宮的決策核心,向來都在邊緣發揮着「打手」的作用,乃俄羅斯聯邦國防部眼中難以共榮且無法患難與共的「阿貓」,同時還是地方軍閥眼中隨時都可摒棄替換的「阿狗」。也正因如此,普里戈任永遠都不可能升格為「俄屬衝鋒隊」的領袖,更不可能如同恩斯特.羅姆(Ernst Röhm)般左右黨內權力平衡的演變與國家內外的發展方向,但終將難逃被拋棄的悲慘命運,即兔死狗烹之典故重現。
為權獻位的瓦格納黨人
在此次為期二十四小時的戲劇性「羅斯托夫之變」中,無論是扛起「反叛大旗」的普里戈任還是決心「斬草除根」的普京,均異口同聲地將矛頭指向俄羅斯聯邦國防部。例如,前者的發難之由就是單方面所宣稱的「軍方突襲」,而後者的講話重點則是已有前車之鑑的「軍方嘩變」,即永久扭轉俄國國運的血腥一九一七年,或盜走俄國偉大勝利與國際大國地位的內戰元年。仔細回想「瓦格納叛亂」之全過程,不難發現普里戈任根本無意顛覆或挑戰普京之權威,相反卻在毫無邏輯可言的亂棋布局中人間蒸發,彷彿流星穿越克里姆林宮上空,為普京實現其遠大政治目標提供了先決條件。
首先,根據俄國歷史發展之政變慣例,在帝國心臟策劃並發動意想不到的軍事行動,且在第一時間以最快速度擒拿帝國元首或最高領袖,雖非唯一先決條件,但卻是決定政變成功與否的關鍵之所在。無論是十九世紀初期計劃在聖彼德堡樞密院廣場迫使沙皇尼古拉一世退位的十二月黨人,還是二十世紀初期劍指臨時政府所在地聖彼德堡冬宮並活捉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布爾什維克,或二十世紀末期為挽救蘇聯舊制度反向選擇軟禁戈爾巴喬夫且逐一控制首都莫斯科所屬各最高權力機構的亞納耶夫黨人,均無一例外地奉行了千年不變的「擒賊先擒王」原則。
相比之下,普里戈任所代表的瓦格納集團並未像十二月黨人般在莫斯科紅場突如其來地給普京一個措手不及,也沒有效仿布爾什維克直接了當地消除前朝所遺留的所有禍根及源頭,更沒迅速掌控普京本人或封鎖佔領莫斯科,反而選擇在鞭長莫及的南俄草原(西欽察草原)之頓河畔羅斯托夫「作秀」,敲山震虎並先發制人,為彰顯克里姆林宮最高權力之威嚴並提供法統依據,進而穩固了雙頭鷹所佔之歐亞版「偉大羅斯」的地緣政治基礎。
延續正統的瓦格納精神
其次,由普里戈任所高調開啟的這一場俄國史上最為短暫的「反叛活動」,憑藉其難以預估的軍事總體實力與涵蓋範圍,成為蘇聯解體以來歐亞大陸「心臟地帶」最為透徹且最為難解的小範圍地緣政治事件,其規模之小根本無法與沙皇俄國時期的任何一場哥薩克地方武裝叛亂或蘇聯解體前後的車臣獨立戰爭相比較,但實質意義與影響力則需另當別論。
之所以將「瓦格納叛變」稱之為蘇聯解體以來影響範圍最小的地緣政治事件的主要原因,在於瓦格納軍事集團乃克里姆林宮所塑造之「Z」字型新愛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繼承者,而非「俄版狼穴計劃」的策劃者。準確地講,全副武裝的瓦格納軍事集團乃普京所延續之「莫斯科羅斯」的堅實捍衛者,是捍衛分別由「莫斯科維亞」與西伯利亞所構成之二十一世紀「羅斯利亞」的屠龍英雄,即偉大聖喬治。對瓦格納所屬俄羅斯籍或俄羅斯裔官兵而言,為捍衛「新俄羅斯」的完整而下火海乃軍人義務,為保衛「莫斯科維亞」的統一而上刀山乃個人職責,為堅守「莫斯科羅斯」之正統地位而戰死沙場乃公民榮耀,而為「羅斯利亞」挺身而出則是每一位俄羅斯兒女所應當履行的民族使命。
難以實現的瓦格納使命
實質上,「瓦格納叛變」事件為克里姆林宮決策核心合理解散該組織鋪平了道路,其主要原因則與俄國當前的國內外局勢密切相關。從內政上看,克里姆林宮面臨着與日俱增的財政與戰略壓力。財政方面,因受西方發達國家及其所屬民主陣營強而有力的經濟與科技制裁影響,俄國外匯儲備規模逐日萎縮,以及戰時國內軍工業重構所需之技術與資金輸入管道基本受阻,導致克里姆林宮不得不狠心拋下自身難以承擔的部分額外「帝國遺產」(即瓦格納軍事集團),借此最大限度地減輕俄屬歐洲板塊單方面所承受的經濟負擔,進而為光復「莫斯科維亞」創造有利且安全的發展環境。
戰略方面,瓦格納軍事集團(融歐派)與俄聯邦國防部(歐亞派)之間的戰略矛盾與利益分歧日益尖銳,迫使身處歷史風口浪尖上的克里姆林宮決策核心不得不調解這一根本無法解開的「死結」。在瓦格納軍事集團眼中,「莫斯科維亞」的利益高於一切,而對於俄聯邦國防部而言,西伯利亞的安全重於泰山。
值得一提的是,兩者之間這一截然相反的國家戰略安全觀甚至都已呈現在俄烏戰場上。歐亞派軍官團認為,這場戰爭是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東斯拉夫正統之爭,完全不同於全民性的反法西斯戰爭,其本質相差甚遠,因此無需充當克里姆林宮的炮灰。融歐派僱傭兵團則堅信,俄烏之爭乃決定「莫斯科羅斯」最終何去何從的終極一戰,絕不可怠慢或鬆懈,無論如何均須背水一戰,毫無妥協之餘地。
相反,從國際角度來看,伴隨烏克蘭危機的逐步升級與俄烏戰事的全面爆發,瓦格納軍事集團所能扮演的「拯救者」形象不僅已黯然失色,且在北約各成員國及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高度警惕下也已無用武之地,如同累贅般持續影響克里姆林宮與俄聯邦國防部及外國政府間的協調溝通。因此,普京「收編」瓦格納軍事集團一方面等同於將其解散,消除了克里姆林宮與其國防部之間的「障礙」,另一方面則等同於向北約與東歐板塊各鄰國「拋出」橄欖枝,表示構成「俄國威脅論」和「俄裔威脅論」的始作俑者就此被取締,區域大國關係之全面正常化指日可待,而俄羅斯民族國家建構進程也受此影響步入新關鍵時期,以烏拉爾山脈為邊界線的「俄版一國兩制」,即分別以俄羅斯族為主體的「莫斯科維亞」(羅斯利亞)及草原民族為主體的西伯利亞(韃靼利亞),將成為維繫歐亞帝國統一的新地緣政治及經濟根基。
(作者為哈薩克國立大學經濟科學碩士、武漢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