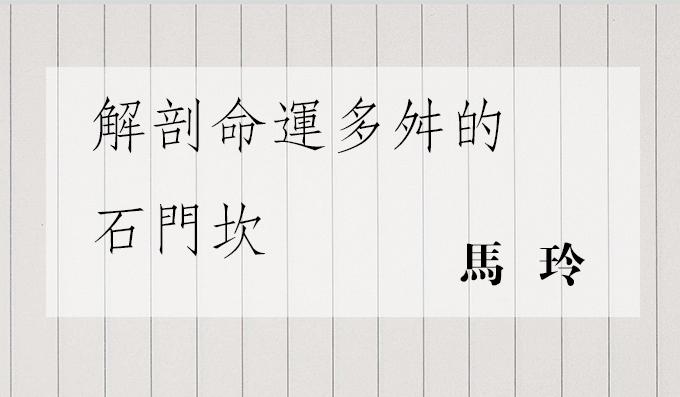社會.時事
貴州與四川和雲南接壤的西北角,有一個少數民族聚集的窮地方,名字叫石門坎。回望這裏發生的起伏跌宕的一百年,不由得生出一種「跌掉下巴」的感覺。
中國絕大部分人對這裏發生的一切聞所未聞,只是最近因為「村BA」和「村超」兩項球事,讓國人突然把目光集中到了這個苗族、彝族和侗族聚集的邊塞山村。
為什麼在這個邊塞山區能搞出國際體育大賽的氣勢?為什麼如此紅火的「村味賽事」在別的鄉村搞不起來?
不說你不知道,說了你可能嚇一跳。
這個地方足球這麼牛,最初的扎根來自於一位英國傳教士,他叫柏格理。百度百科對他的評價是:創制苗文並極大地影響了苗族的歷史發展。
柏格理與苗族教育
百度百科對石門坎的歸納是:一九○五年,隨着英國傳教士柏格理的到來,這裏迅速成為「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區」,中國現代教育水平最高的地方。在上個世紀的前半期,石門坎是苗族文字的發源地,是雲貴川交界地區的教育中心、農耕技術推廣中心、苗族文化的傳播中心、戰時災民自救中心、麻風病等地方病的救助中心,還是足球之鄉……話說一八八七年,柏格理二十三歲時受召來到中國傳教。除了傳教,他還和妻子創立了「天足會」,在滇黔川山區倡導放開小腳。他不認同八股教學,於一八九三年改教會私塾為「中西學堂」,在當地開設天文、地理、英語、算術等課程。同時創辦了女子識字班夜校,開了許多風氣之先。一九○五年七月十二日,居於威甯和水城的四個大花苗人,跋山涉水行走數日後,找到了身在韶通的柏格理。當年冬天,柏格理來到了石門坎。
他穿苗服、說苗語、住苗家、睡臭蟲跳蚤成群的麥草堆,逐漸成為苗民最可信賴的人。苗族沒有文字,歷史靠口口相傳。柏格理帶領數人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結合苗族衣服上的符號花紋,創立了簡易的拼音文字。當地人為區別一九四九年後創立的苗文,稱其為「老苗文」,西方則稱為柏格理文。一九○六年,柏格理開班授課,二十多個學員全是成年教徒。其後,雲南威縣、鎮雄、楚雄,甚至紅河的苗族學生都趕來就讀。一九○八年柏格理回英國療傷時募集了二千英鎊,回石門坎後修建了一幢有煙囪壁爐、可容納兩百多人的教學樓,正式成立了石門坎小學。在獲得循道會的津貼後,又相繼修建了宿舍、禮堂、足球場和游泳池,還舉辦過運動會。
「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環模式
一九一五年夏,「傷寒」傳到石門坎,很多苗民和學生病倒了,柏格理把崖下的山洞當作隔離室,他在那裏守護着病人時不幸被傳染,於九月十五日病逝,時年五十一歲。據地方誌記載,他出殯時,苗、彝、漢送殯者達好幾百人,都痛哭失聲。他在石門坎十一年扎下的根,即使他本人離世而去,但依然在開花結果,那時他已培養出一批苗族老師。
一九○五年以前,石門坎苗族略通文字的只有在土司家做高級家奴的倆人;到了一九四九年,這裏有四千多名小學畢業生,幾百名初高中生,三十幾個大學畢業生,還有兩名博士(也有說產生了四位苗彝博士)。第一個博士是一九二八年石門坎走出去的學生吳性純,他獲得美國醫學博士後回到石門坎。之前,柏格理不僅在教堂裏開了藥房,還從英國帶來一批小刀和疫苗給村民種牛痘,另外也為麻風病患者建立了收養中心。這位醫學博士要把柏格理開創的醫學事業進行下去。他辦了平民醫院,開了護理學校,在山區扎實從醫。一九三五年,從石門坎走出去的苗族人朱煥章從成都華西大學畢業,婉言謝絕國民政府重慶行轅的職邀,回到石門坎行醫辦學,教書育人,直到五十年代去世。
一九三四年,石門坎搞的運動會盛況空前:兩萬餘人參與。比賽時,學生對學生,農民對農民。光華小學的足球和長跑項目每每奪魁,石門坎被稱為「貴州足球的搖籃」。
曾任國民政府重慶市長的大軍閥楊森,專程去石門坎參觀過,他看到足球場大為驚訝,就令他的隨行人員與石門坎學生進行足球比賽,連賽三天,都是石門坎學生獲勝。據說,楊森帶走了四個學生隊員。並送了一批球鞋給石門坎學生。
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奧運會上,中國足球隊中就有來自石門坎的隊員,一九五九年的國家足球隊裏石門坎人也不少。
這裏的學生和許多教民都會說英文,國外的信件可直接寄到這些偏僻的山村,他們能看懂英文信件和報刊。抗戰時,曾有美國援華飛行員被日軍擊落在該地區,苗人救下飛行員並用流利英文與他交流。當年的石門坎已蜚聲海內外,國外來信上只要寫「中國石門坎」就能準確送達。
至到一九五○年,石門坎管理着九十六所小學、五所中學、一所神學校和一些醫療機構。石門坎的教育,已經輻射到臨近的幾個鄉縣。這些學校的教師,許多都是從石門坎畢業的學生,在外面接受了更高一級的教育後返回的,柏格理最初就設計了「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環模式。
苗族是很老的民族。其祖先是與黃帝炎帝並稱「中華三祖」的蚩尤,遠古時因戰敗被擠壓到山野邊陲。從他們落腳的地名「威寧」、「昭通」、「武定」、「鎮遠」即可看出,他們不易被「馴化」,但這裏的苗族在傳教士的感召下卻走入了文明。
一九五○年以後,石門坎又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傳教士全都被清走了,基督徒被關進牢裏了,老學校和醫院漸次關閉了,山民的後代因輟學又成為文盲了。
曾任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的陳浩武博士,因為對「石門坎現象」抱持強烈的關注,不僅親自到那裏去踏足尋訪,而且成立了深圳市石門坎教育公益基金會,自任理事長。他說:「石坎門曾被稱為西南地區的耶路撒冷,但一九五二年以後呈拋物線向下。一九八八年的調查顯示,石門坎地區的文盲率佔百分之八十八,貧困率百分之九十八,重新回到了蠻荒。這從兩個維度證明了信仰和教育的意義,前面的五十年和後面的五十年,正反兩方面加以證明。」
他描述道:「經歷了半個世紀的自然災害和政治洗禮,許多老房子化為殘磚碎瓦,許多老人消失在塵埃裏。今天來石門懷古,已經難覓當年『我華校旗樹黔疆』、『齊聲高唱大風泱泱』的盛況。」
五十年代以後,教堂式微,學校也停止講授苗文。新苗文創制出來後,老苗文逐漸散落民間,棲身草房漏簷之下,父子相傳、夫妻相傳,借助於地緣和親緣網絡頑強生存。甚至在與石門坎遠隔數百里外的畢節、納雍、武定,在千山萬壑中,在苗家茅草屋裏,我都遇見了老苗文的行蹤。雖然給一雙雙黑黢黢的手呵護得發皺,給一個個沾着泥土的衣袖摩挲得變黑,那些寄託了苗族情感的文字依然面目清晰,靜靜注視着世界。
另外,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和博士研究生導師沈紅,以組織與制度變遷研究室主任的身份,也曾專門到石門坎做田野調查,寫出了《一個村落的本土與世界》。
歷史的活化石
不過,陳浩武的基金會也好,沈紅的調查報告也好,除了相關機構和人員以外,社會上知道的人很是小眾,大部分中國人連石門坎這個名字都沒聽說過。
現在「村BA」火了,「村超」也火了,但石門坎依然寂寂無名。
看到新華社昨天發的一篇文章,借着這股「火」,他們派出了調研組奔赴貴州榕江縣和台江縣進行採訪,為的是探尋「兩江賽事」衍生出的一個個和美鄉村故事。採訪報道隻字未提石門坎,只提到《榕江縣誌》、《榕江文史資料》相關記載告訴調研組:「榕江人抗戰時就接觸足球了。那年月為避戰火,先後有三所學校遷到榕江。」文章說一九三九年冬貴州師範學校遷入後,短短幾天就把一個簡陋足球場建好了;一九四四年廣西大學和桂林漢民中學遷來,更多學生把熱愛足球的種子撒在這個偏遠小城。此後,足球與榕江便緊緊相連了。
我本人就是媒體記者,我認為記者要遵循的最基本職業操守就是,「尊重事實,客觀報道」。讀者只有知曉了整個歷史脈絡,才有可能理解為什麼這山野裏的籃球和足球這麼火,為什麼別的鄉村山野卻效仿不來。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沈紅到石門坎進行田野調查後寫的《一個村落的本土與世界》,從社會學角度講,具有罕見的歷史價值。我讀研時學的專業便是社會學,「石門坎現象」具有從社會學角度深入研究和挖掘的意義。
十年前,我曾隨一個記者團到黔西南一帶參觀,看到那塊多民族雜居之地,充滿特色但也確實貧窮,有個苗族婦女在一個角落拉住我,稱兒子在外求學缺學費向我要了一些錢。
解剖這個命運多舛的石門坎一百年經歷,就猶如看到了一個別具色彩的活化石。後人的客觀認知,其實也是在還原它的自然本色。
在貴州偏僻的山區,「村超」在球場上踢出了貼地斬、圓月彎刀、彩虹過人、電梯球等專業技巧,本鄉本土農民擔任的球賽解說員亦不次於專業人士。這些球賽還帶火了山鄉旅遊,各種小店裏的「村BA」文創產品和苗族銀飾比比皆是,那些印有「村BA」標誌和苗族圖騰的球衣球襪以及足球和籃球,都頗受遊客喜愛。
人類,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你來我往,共同融合,是不可改變的歷史,也是不可逆轉的未來。
(作者為本刊特約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