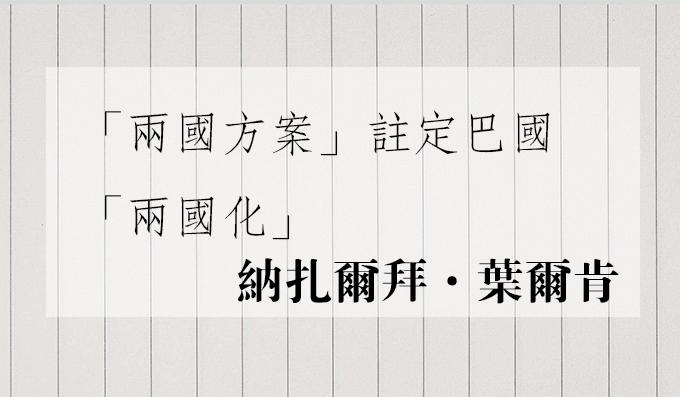社會.時事
開啟於今年十月七日的「阿克薩洪水」之新型滅猶主義恐怖行動,自發動之日起就已告知世人,亡於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反猶浪潮以海嘯般的速度自東向西再度席捲整個歐亞大陸,由無數鮮血所鑄成的「中東民主孤塔」以色列正面臨着自納粹猶太大屠殺以來最大的歷史考驗,偉大應許之地與神聖自由之靈能否屹立不倒且永生不滅,完全取決於公民正義的延續,而非國之永恆。
眾所周知,亞伯拉罕三大子孫(猶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心目中神聖不可侵犯的耶路撒冷在千年歷史長河中,一次又一次見證了多個多元文明因虔誠與寬容興起繁榮,也反覆地目睹了無數單一政體因墮落及貪婪自滅,包括猶太聖殿哭牆、基督聖墓教堂及伊斯蘭阿克薩清真寺在內的偉大聖蹟自始至終都在告誡後人,上帝所賦予之「特選子民」並非特權,而是恩賜,其核心是懂得共存共榮,而非你死我活,任何視人命如草芥的殺孽之行無一例外均必遭天譴,並殃及子孫後代且永不得翻身。
恐襲計劃的規劃導向
在解讀恐怖組織哈馬斯所發動之「阿克薩洪水」行動的軍事總體戰略方針與地緣政治整體目標時,需首先注重其名稱所賦予且概括的基本意識形態內涵,即分別由「阿克薩」與「洪水」對接而成的一點多步走式布局規劃。
顯然,「阿克薩洪水」計劃中的「阿克薩」表面上來看既象徵哈馬斯本身,又代表以東耶路撒冷為建國目標的整個「巴勒斯坦」。但將其與「洪水」一併掛鈎時可隨即察覺到,這僅僅是以耶路撒冷為中心沿東西兩側之以色列與約旦河西岸逐步向外蔓延的一場「世紀暴雨」,其程度絕不亞於聖經所記載的「挪亞洪水」。
反之,既然是「世紀洪水」,且以「阿克薩」為起始點,不難看出「徹底淹沒」定都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和實際控制約旦河西岸地區的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組織)是哈馬斯所執行之一點多步走戰略規劃的第一步,同時也是引發全球性骨牌效應的關鍵一步,即通過「解放巴勒斯坦」之名發動足以使以色列與法塔赫瞬間反目成仇的轉嫁危機式軍事行動,進而觸碰刺激各方背後所屬不同域內外勢力的「敏感神經」,迫使其出於捍衛各自利益而相互「討伐廝殺」,並藉此最終構建出有利於隔岸觀火之「始作俑者」的國際版「百家爭鳴」時代。
分離邊緣的巴勒斯坦
實現以巴「兩國方案」的關鍵在於誰是未來區域所屬國際型公認「巴勒斯坦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反向理解就是地處飛地加沙地帶的恐怖主義組織哈馬斯與長期穩坐於約旦河西岸部分地區的法塔赫之間誰真正有資格或能夠全面有效地代表未來國際所公認的「巴勒斯坦國」。
顯然,「誰是巴勒斯坦唯一合法代表」與「誰是巴勒斯坦唯一合法政府」這兩大地緣問題無論對聯合國本身,還是其已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的成員國而言,都是難以左右逢源的「利弊問題」,稍有不慎將會引火焚身,而倉促且無序的以巴「兩國方案」則會間接造就中東巴勒斯坦版的「一邊一國」或「兩個巴國」,使之成為巴勒斯坦人民世代仇忌於心的現代版新型「最終解決方案」。
與之不同的是,對於手握「阿拉法特的遺產」的法塔赫當前領導人阿巴斯而言,哈馬斯所發動的「阿克薩洪水」是其終身未料之千年一遇「十災」的開端,乃名副其實的滅頂之災。其中,由於哈馬斯深知以色列會強而有力的實施自衛,因此斷定反恐過程當中所難免出現的非戰鬥人員傷亡慘狀,將會以「血的代價」催生出更加猛烈之「生的仇恨」,進而以「第一災」的形式蔓延至包括巴勒斯坦在內的整個穆斯林世界,致使法塔赫沉陷於「血海深仇」中緩慢且被動地喪失原有道義法統與歷史正統地位。
東方式滅猶觀的利弊
哈馬斯籌劃之「阿克薩洪水」所屬「第二災」與「第三災」須建立在新一輪全球性滅猶思想與反猶浪潮中方可實現,即在以色列國防軍的沉重打擊下有組織地「化整為零」,開啟民族統一大業中永載史冊的嘗試性反圍剿「全球遠征」,途中高舉「雙反大旗」(反猶反以)並獲取世界,包括非穆斯林人士在內,所有極端「兩面人格」集團的技術及資金支持,進而自我全面伊斯蘭國化,後再以約旦河西岸法塔赫政權為顛覆之「合法最終目標」,持續不斷地通過域內外各公開及秘密「落腳點」實施地下滲透,需要時恭順「幕後指使」,必要時則反咬「實質金主」,反向高舉「聖戰大旗」且劍指「卡菲爾國」(異端邪說者與無神論者),而非任其擺布。
綜上所述,「阿克薩洪水」所開啟之「十災」的前後順序分別是審判式的「暴雨雷鳴」、重生式的「自我犧牲」、預謀式的「逆流而上」、逢源式的「落葉生根」、化緣式的「搜刮搶掠」、詆毀式的「高聲讚頌」、開明式的「指鹿為馬」、聖賢式的「煽風點火」、反問式的「開疆闢土」和行軍式的「問鼎天下」。須警惕的是,哈馬斯歸根結蒂都是顛覆式的恐怖主義地方割據勢力,任其不受約束地遍地開花或政權合法化,等同於助長國際恐怖主義再度抬頭,以及承認國家恐怖主義的現實存在。
應切記,今日以色列所遭遇的是未來世界各國都可能面臨的人為慘劇,昨日的「將猶太人趕回大海」這一沙文主義式滅族口號必定會成為明日的「將卡菲爾趕出聖地」之新型正統國號,而依舊尚在的「將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這一帝國主義式滅國信念必會變本加厲地轉變為「狂犬患者」的最終歸宿,無一例外。
究其原因,以色列絕不會對霸權低頭,建立在自由、公平與公正基礎之上的民主社會將義無反顧地捍衛每一位公民與生俱來的生存權力,無論其出生、種族還是信仰都一視同仁,而堅不可摧的偉大公民則會齊心協力捍衛屬於自己的神聖國度,如同斯巴達三百勇士般持續不斷地抵禦東方的再度入侵,即使犧牲也在所不辭。以色列的立國根基是持續強大且穩固不移的多元共存式現代民族國家所應具備的公民制度,而非子虛烏有的古老不間斷式偉大帝國專制。
不可遺忘的先祖遺訓
阿拉伯諸國眼中懸而未決的「巴勒斯坦問題」向來都具有難以直視的兩面性,既是「福」又是「禍」。難以直視的原因在於,所謂的「阿拉伯世界」自古以來就是一盤散沙,歷史上唯一使其實現短暫統一的即是穆聖,而偉大也因此自始至終都屬先知穆罕默德一人所享有,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穆聖通過仁慈和包容化解了半島阿拉伯部落間的殘酷與仇恨,使其明確意識到女性乃生命之母,同時也是真愛的捍衛者兼真理的傳遞者,其地位神聖不可侵犯。除此之外,不分膚色五湖四海之穆斯林均為兄弟,而手握先知穆薩(摩西)與以撒(耶穌)所遺留之聖典的猶太人與基督徒同屬持經人,應受共奉易蔔拉欣(亞伯拉罕)之神的穆斯林保護,而非迫害或屠殺。
中東之亂的禍根之源
在中東傳統三角鄙視鏈中,無論是伊朗波斯人還是圖蘭突厥人均視「阿拉伯世界」為可有可無的抽象存在。對波斯人而言,隔海相望的「阿拉伯人」充其量也就是古代從荒漠中長途跋涉勉強走出開化的「蠻夷」,以及當代完全不知天高地厚的「暴發戶」,毫無文化底蘊可言。而在突厥人眼中,遍布商路各大城市中的「阿拉伯人」乃見錢開眼的「偽君子」,國難當頭之際可毫無保留地充當「小人」這一量身定制的特殊角色,且在不知大局為何物的前提下,不僅慣於引狼入室且異想天開,純屬有名無實的「烏合之眾」。
即便如此,伊朗與圖蘭的後繼者們始終認為穆聖為世間之最後先知,堅信穆斯林是宇宙真理的擁有者,造物主的獨一性毋庸置疑,伊斯蘭乃偉大盛世的搖籃與泉源。但日益墮落的阿拉伯歷代哈里發則讓他們無比失望,甚至都不願強調穆聖的阿拉伯出生,後者貪得無厭且自私透頂的劣性不僅招致懲罰性的滅頂之災,且在遭受「真主之鞭」成吉思汗的毀滅後也未曾悔改,歷代碾壓烏瑪民主的半島獨裁者正是葬送伊斯蘭輝煌,並使之一蹶不振的罪魁禍首,同時也是當今「巴勒斯坦問題」懸而未決的始作俑者。
(作者為哈薩克斯坦歐亞國際關係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