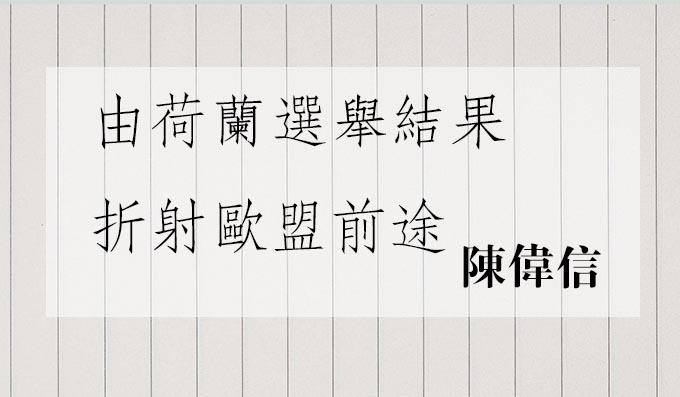社會.時事
去年十一月荷蘭舉行國會選舉,選出國會二院(Tweede Kamer der Staten-Generaal)共一百五十個議席。在民調最後階段領先的「極右」政黨自由黨(PVV)成功將支持度化為選票,以近百分之二十四的得票率獲得三十七席,成為國會二院的第一大黨。至於原首相呂特(Mark Rutte)所屬的自由民主人民黨(VVD)則以一席之差成為國會第三大黨。
自由黨「突襲」成功,似令歐洲政壇再次蒙上「極右當道」這片不受國際社會歡迎的陰霾,畢竟波蘭選舉極右法律與公正黨(PiS)雖保留第一大黨地位,但前歐盟高峰會(European Council)主席圖斯克(Donald Tusk)所領導的公民平台(Platforma Obywatelska)卻成功組織政府。本以為會失去一個重要的政治盟友的匈牙利總理歐爾班(Orbán Viktor),卻在荷蘭選舉結果中找到一線曙光︰自由黨黨魁維爾德斯(Geert Wilders)的反移民、反伊斯蘭、疑歐立場成功在歐盟始創國荷蘭立足,更是為極右派本年六月歐洲議會選舉注入一枝強心針。
「荷蘭特朗普」︰由富圖恩說起
儘管國際及本地媒體均以「荷蘭特朗普」來形容維爾德斯,但筆者認為荷蘭政壇與美國政壇幾乎沒有任何可比性。與其說維爾德斯是仿傚特朗普,倒不如說他是荷蘭第一代激進右翼政治家富圖恩(Pim Fortuyn)政治遺產爭奪戰的最終勝利者。富圖恩這個名字對本地讀者而言相對陌生,但在荷蘭當代政治史卻佔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席位︰富圖恩本是馬克斯主義社會學教授,早年進入政壇時也加入屬社會民主主義的工黨(PvdA),但他在政壇打出名堂的卻是他的反伊斯蘭移民的觀點,而這些觀點也令荷蘭的「極右」思想,與由天主教保守主義(如匈牙利及波蘭)所主導的「極右」思想,有着本質上的差異。
富圖恩主義(Fortuynism)固然有激進右派的基本元素︰反精英主義、國家及民族優先、反官僚主義及直接民主制等針對荷蘭舊政治階級的主張,但它與東歐地區或天主教保守主義主導的「極右」思想也有着明顯不同。例如富圖恩是一個公開的同性戀者,因此他的政綱支持不同性取向平權,與意大利、法國、波蘭、匈牙利等以傳統家庭崗位及價值作為其右翼思想基礎大為不同。其政治遺產繼承者維爾德斯雖然沒有公開表達他對性向平權的立場,但其政黨的政綱多年來將性向平權與反伊斯蘭文化立場掛鈎。事實上,這也是荷蘭「極右」與其他歐洲國家「極右」的另一個不同之處,就是伊斯蘭文化塑造「保守」及「落後」的思想文化,因而與荷蘭社會所代表的「開放」及「多元」不符。例如在政教問題上,富圖恩及維爾德斯均認為伊斯蘭教不單純是宗教而是一種近乎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維爾德斯甚至於二○○七年將伊斯蘭教聖典《古蘭經》與希特勒經典著作《我的奮鬥》(Mein Kampf)等同,認為這些都是代表法西斯主義的著作應當禁絕於荷蘭社會。
然而從選戰角度分析,自由黨及維爾德斯(以及富圖恩)不過是將荷蘭內的穆斯林社群視為選戰時的「稻草人」︰透過將穆斯林社群聯繫歐盟及荷蘭政府的建制精英政治,強化自由黨作為草根、直接民主及主權在(荷)民的標籤;透過將伊斯蘭文化塑造成「落後」文化及對荷蘭社會身份認同的威脅,強化自由黨作為荷蘭「進步」及「開放」文化身份的守護者角色。因此,當民調愈顯示自由黨有機會成為第一大黨時,維爾德斯的反伊斯蘭政綱便愈見軟化,甚至在順利取得第一大黨地位後,表示現階段有更多關於荷蘭社會關注的民生問題要處理,有關穆斯林社群去留、脫歐公投等涉及憲政爭議問題可暫時放下—因而被荷蘭媒體戲謔為「懷(柔)」爾德斯(Geert Milders)。一如所有歐洲極右政團一樣,它們在選舉制度及選舉結果的誘因下,在尋求權力的過程中也會選舉走向中間化。
被簡化解讀的荷蘭選舉結果
這種「極端主義中間化」的政治操作,在荷蘭的選舉制度、組閣文化以及廣義的政治文化被進一步放大。與香港市民「習以為常」的英美選舉制度及文化不同,荷蘭是少數實行全國單一選區的國家,全國一百五十個國會二院席位以全國不分區比例代表制方式選出。由於荷蘭的當選門檻相對低,因此荷蘭國會絕對稱得上是「五光十色」。為了讓國會不致於過分碎片化難以組織政府,荷蘭的選舉制度是採用對大黨相對有利的漢狄法(d’Hondt method),因此相信自己有機會執政的政黨會盡量在選舉最後階段爭取最多選票,為日後的組閣階段爭取更多的籌碼。因此,當我們審視這次選舉結果時,我們要問自由黨的異軍突起,是受惠於右翼總體得票上升,還是右翼陣營的內部轉移?根據荷蘭廣播聯盟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自由黨有百分之十二的選票是在二○二一年選舉沒有出來投票的選民,百分之十三在二○二一年選舉投票支持其他極右政黨,百分之十五的選票是來自二○二一年投票支持自由民主人民黨的選民,而二○二一年及二○二三年均投票予自由黨的佔百分之三十九。百分之三十九是一個怎樣的數字?大抵就是二○二一年自由黨所獲得的總票數。
當時的民調更多是集中討論由基督教民主黨(CDA)走出來的新政團新社會契約(NSC)、自由民主人民黨及綠色左翼—工黨聯盟會脫穎而出,成為國會第一大黨獲得優先取閣權。新社會契約在八月公布參選後,先是吸收早前在國會一院及地方選舉表現出色的農民—公民運動及部份自由黨的選票—這些選民的特色是他們對自由民主人民黨過份的執政,例如綠色政策及移民政策十分不滿,卻在過去眾多政治光譜中找不到可代表自己的政治人物。新社會契約的反建制精英立場、左翼的經濟及社會福利政策、右翼的移民立場,以及提出「良好管治」為執政基礎,幾乎徹底蠶食農民—公民運動的選民基礎,也吸引部份不認同自由黨及另一極右政黨民主論壇(FvD)的激進主張的右派選民。然而,隨着新社會契約領導人奧姆齊赫特(Pieter Omtzigt)在辯論及選前表現不濟,加上在成立之初曾提出不希望擔任總理,令部份支持者考慮在最後關頭轉變陣營—選舉工程表現出色,立場變軟的「懷」爾德斯變成為這些「憤怒選民」的最後答案。
另一方面,自由民主人民黨領袖耶希爾格茲—澤赫里烏斯選前有意無意之間表示不排除與自由黨合組政府的可能性—這是原首相呂特不會(也不敢)打開的「潘朵拉盒子」。耶希爾格茲—澤赫里烏斯的取態進一步增加維爾德斯及自由黨的認受性,特別是那些不滿自由民主人民黨移民立場的支持者,以及在過去數年認為政府無力解決經濟及民生問題的選民,希望以改投自由黨來逼使政府作出改變,而其他反建制、反移民、立場激進右翼的選民,見到自由黨成為第一大黨的可能性時,也自然選擇「西瓜靠大邊」(bandwagon),策略投票支持自由黨搶得執政主導權。因此,自由黨這次選舉勝利並不代表自由黨原來相信的極右立場在過去數年有長足的支持度增長,而言一連串政治決策失誤、個人表現不濟,以及維爾德斯的極右立場軟化的技術性調整結果。是否如歐爾班所言「風起了」(the winds of change are here),仍有待時間驗證。而維爾德斯面對的第一個考驗,自然是軟化了的政治立場能夠為他換來順利組閣的機會。
荷蘭是歐盟政治未來的縮影
儘管筆者的立場是不必要將維爾德斯在這次荷蘭選舉的成功放大為整個歐洲政壇右轉的結論,但荷蘭選舉結果對歐盟政治及經濟前景卻有一定的指標作用。畢竟歐盟政經特色可說是荷蘭「圩田」模式(polder model)的進階版︰在不同政策領域既有「資本階級—歐洲執委會—勞動階級」的產業共識政治,也有「左翼政府成員國—歐盟理事會—右翼政府成員國」的國家共識政治;而歐盟面對的政經問題也是荷蘭面對政經問題的進階版︰農業大國烏克蘭加入歐盟對歐洲家庭農業有何衝擊,經濟水平發展較低的候選國加入後如何影響歐盟財政資助分別,歐盟繼續東擴如何影響歐盟管治,來年歐洲可能再一次面對結構性通貨膨脹及美國息口走勢如何影響歐洲經濟及民生事務等,都足以影響本年六月的歐洲議會選舉結果,以及歐盟下一個五年的政治經濟發展路徑。
當然,在歐盟級別的「圩田」模式,歐洲的極右派要奪權主導歐盟政治,比維爾德斯成為荷蘭首個極右派首相更為艱難。儘管筆者預期六月的歐洲選舉疑歐右翼的得票及議席數均有所上升,令歐盟高峰會在考慮歐洲主要政治職位時多了一點點的變數,但正如維爾德斯在面對選舉也會變成「懷」爾德斯,疑歐右翼所追求的歐盟改革在選舉及資源分配面前也會變得務實。事實上,即使所謂的「法德軸心」也謀求歐盟有所改變,歐盟與成員國之間的權責分配、國家產業資助及歐元區財政紀律的平衡,歐盟在中美之間的角色,以及如何處理新成員國與既有成員國的經濟、政治及外交磨合等議題,歐洲右翼及其代表的歐洲民眾,也是歐洲政經發展的持份者,總有一天歐洲政治精英需要打開這個「潘朵拉盒子」。歐洲及荷蘭民眾需要做的,其中是相信民主體制及共識政治的韌性,相信中間派與激進派的對話中會找到一條屬於荷蘭以及歐洲的治國之道。
(作者為諮詢公司Orientis(Hong Kong)研究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