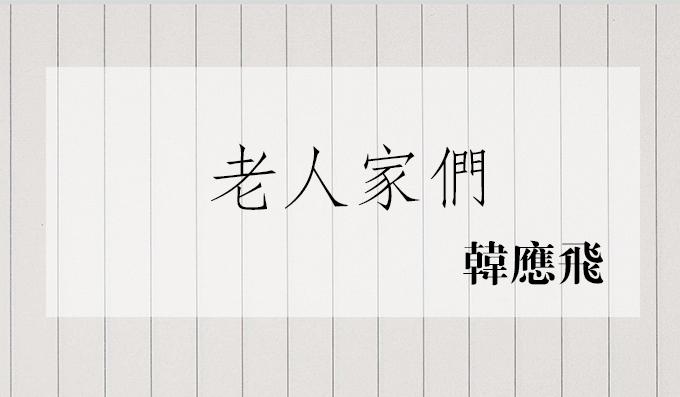心田集
還在二十二三年前,妹妹就批評我:「交往的人,不是大學生,就是老年人。為什麼不多和同年齡的人交往呢?」
那時,我三十多歲,學生們小我十七八歲,老年人們大我十幾二十幾歲。二十二三年後的今天,我自己也快到老年了,而當年的那些老年人,有的八十來歲,有的七十多歲。可是,我還是和這些老年人有交往。有時,回顧這二十多年的人生,也會感到和老人家們的交往,浪費了自己人生中的寶貴時間。但有時也想,這二十多年和他們的交往,雖然不願意看作是自己人生的一部分,但至少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二○二三年十月底,我連續三天,見了三位老人家。
第一天的K女士,原是一家著名雜誌的編輯,十年前在追悼著名作家納達伊納達的聚會上相識,一直保持交往。那天早上,她給我打來電話,問我願不願意去參加紀念著名作家辻邦生百年誕辰的相關活動。我原本就打算去的,所以立即回答:「去。」她說,那十二點在目白站見面吧。
十二點見面後,我們先去車站附近的咖啡館吃三文治。K女士不讓我付錢,她說:「今天是我邀請你的。所以,我來付錢。」金槍魚三文治,我很少吃,這天吃,意外地好吃。我向K女士談起了前些日子見到她的一位晚輩校友—著名紀錄片導演的事,也因此互相說了不少我們多年來一直最為關注的話題:核電問題。
不知為什麼,那天,我帶了即將和我開始新生活的C女士的幾張照片。K女士聽到我說即將開始新生活,高興得幾乎跳起來,她那喜悅至極的神情,讓我感動。她一邊看着照片,一邊讚美:「優雅的女士!」她又解釋:「這幾年一直想問你,但總覺得是非常個人的事,所以就一直沒問。」
K女士高興地說:「我馬上告訴S女士(K女士的友人,我偶有見面),等C女士來日本時,聚會慶祝!」
接着,她又說:「我的兒子十二月也要結婚,是第二次結婚。五十歲了,對方四十歲。前些天,我和丈夫見了對方的父母,四個人不約而同地說,兒女們組成新的家庭,我們真是放心了!」K女士說到「放心」這個詞時,不由得提高了聲音,表情喜悅,略有興奮。
那天,我和K女士參加了三個半小時的紀念活動後,她領我去她當年工作的雜誌社走了走。我吃驚了。發行量七萬八千冊的百年雜誌《週刊朝日》都已停辦的今天,這家雜誌竟然擁有幾座樓房和一個不小的院子。我對K女士說,看來,經營得不錯!
那天,K女士還給我帶了她親手做的意大利麵條的肉醬,而且詳細講解了和煎雞蛋一起吃的方法。
我說起自己的母親今年七十七歲,K女士說,我比你母親小不了幾歲。K女士大概大我十五六歲,稱她為老人家,也許不太合適。那天她告訴我,十一月中旬要去鐮倉爬山。
和K女士見面的第二天,我和七八年前退休的F先生相隔一年見面。前幾年,即使是疫情猖獗的日子,我和F先生也常見面,而且每次都要吃烤鰻魚。十月底的這一天,我們也照例去吃了烤鰻魚。席間,我拿出幾年前他送給我的一本有關司馬遼太郎的書,說,有一個詞不會念,查了《廣辭苑》等大辭典,也沒查到。F先生笑着說:「我不會念不了吧?!」打開書給他看,他立即讀給我聽,並說,這個詞,辭典上一般不會有。他還給我解釋了意思。那天,我還向F先生請教了美國作家錢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的一句話,他也耐心地做了解釋。
和F先生吃飯後,我們去附近的一家寺院,打算給正岡子規掃墓。但不巧,寺院大門緊閉。F先生很生氣:「佛教的寺院,怎麼能關門呢?」這些年,給現代日語的創始人─正岡子規掃墓,是我們吃烤鰻魚後必定要做的一件事。這天,F先生沒能如願,他說:「子規會原諒我們的。寺院不開門,沒有辦法。」
F先生早年專攻法語,後來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日語,五十多歲時回到日本,在一所私立大學為留學生授課。他除了法國文學和美國文學外,對日本文學也廣為涉獵。近十年來,知我對日本文學抱有興趣,F先生給了我很多文學類的書籍,還具體推薦了池波正太郎、岡本綺堂的不少作品。說實在的,這兩位作家的作品,如果不是F先生推薦,我大概至今都不會閱讀。特別是池波作品,最近四五年,我讀了很多,他的幾本散文集,成為我放在枕邊、裝在書包裏反覆閱讀的作品。
那天,F先生還給了我兩大包黑胡椒煎餅,說是妻子讓他帶給我的。大概是前年開始,每次和F先生見面,他都要帶一些吃的給我,也總是說:「妻子讓我帶給你。」F先生的妻子,我也見過幾次,每次都和我談很多,特別是美國和法國電影,也總是帶給我水果和煎餅。
F先生和我母親年齡差不多,近年身體弱了下來。有時,他和我走在大街上,走着走着走不動了,就只好停下來休息片刻。F先生願意和我見面,還經常給我帶些吃的,我只有感激。
和F先生見面的第二天是萬聖節,東京繁華街區澀谷人山人海,我卻穿梭在密集的人流中。那天,應八十五歲的M老師的請求,我去位於澀谷的養老院看她。一年前的這個時候,我去她家看了她幾次。這次,卻是在養老院見面。去之前,問她需要什麼,她說:「帶些柿子和梨吧!」
養老院極高級,相當於五星級酒店。
去之前,我心裏想,這三天,我是在幹什麼?時間都浪費了!但是,和M老師聊了一個多小時,參觀了養老院後,我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心理衝擊:「幾年後,我父母怎麼辦?二十多年後,自己怎麼辦?」我想,這是我那天在人海中穿越繁華街道和M老師見面的最大收穫。
和K女士、F先生、M老師三位老人家,今後也會保持一定的交往。從他們那裏。我是能學到不少知識,也能聽到一些有趣的事。
事實上,這次和K女士見面,她就跟我講了四十多年前去辻邦生家取稿子的事:「那天,我按了門鈴後,大作家辻先生穿著紅色的Gown來開門,他睡眼惺忪,對我說……。」
作者按:辻邦生的百年誕辰是二○二五年,但紀念活動從二○一七年就開始了,稱之為「紀念事業」。我二○一八、二○二二、二○二三年都參加過。
(作者為日本中央大學兼職講師。)